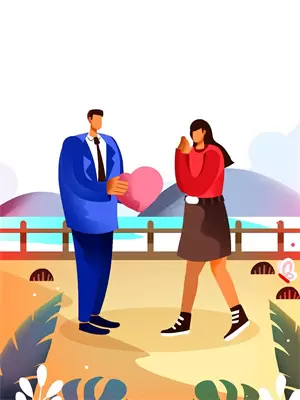又拉着我重见光明那个我最恨的……也是我最爱的人1杨澈站在南开大学美术馆的落地窗前,
指尖轻轻摩挲着手中素描本的边缘。窗外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,
为他轮廓分明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边。再过三天,
这里将举办他的个人作品展——《光之边界》,这是设计系建系以来首次为本科生举办个展。
"杨澈,赞助商对《破晓》系列很满意,说是有商业潜力。"系主任王教授走过来,
拍了拍他的肩膀,"好好准备,这次画展可能会改变你的职业生涯。"杨澈点点头,
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弧度。他知道自己的价值——从大一起就包揽了所有专业比赛的一等奖,
大二时作品被选送参加国际青年设计师大赛,如今已有三家设计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。
他的未来,就像他笔下那些充满张力的线条一样清晰明朗。"对了,你的眼镜呢?
"王教授突然问道。杨澈摸了摸鼻梁,那里空空如也。"镜架断了,刚送去修理。
反正今天只是来确认场地,不碍事。"离开美术馆时已是傍晚,
杨澈拐进校园附近一家名为"暖光"的小餐馆。这家店他常来,价格实惠,光线充足,
适合他这种经常需要赶设计稿的学生。"您好,请问几位?"一个清亮的女声响起。
杨澈抬头,看见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服务员站在面前。她胸前的名牌写着"安雪",
眼睛很大,在餐馆暖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明亮。"一位,靠窗位置。"杨澈说。
安雪领他入座,递上菜单时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水杯。她慌忙道歉,手忙脚乱地擦拭。
"对不起对不起,我今天刚来第三天,还不太熟练...""没关系。"杨澈摆摆手,
目光已经落在菜单上。他点了一份招牌牛肉面和一杯冰柠檬茶。餐馆里人不多,
杨澈拿出素描本,继续完善画展的最后一幅作品。他的手指在纸面上快速移动,
铅笔勾勒出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——那是一个站在光明与黑暗交界处的背影,
正是他这次展览的主题。"您的牛肉面。"安雪小心翼翼地将碗放在桌子边缘,
生怕再出什么差错。杨澈点点头,没有抬头。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画作上,
左手无意识地摸索着筷子。就在这时,餐馆后厨突然传来一声巨响,像是锅碗摔落的声音。
安雪被吓了一跳,身体猛地一颤,手肘撞到了杨澈面前的汤碗。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。
滚烫的牛肉汤从碗中倾泻而出,直接泼洒在杨澈的脸上和眼睛上。
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,双手本能地捂住眼睛,从椅子上跌倒在地。"啊!我的眼睛!
我的眼睛!"杨澈在地上痛苦地翻滚,周围的人全都惊呆了。安雪脸色煞白,
站在原地一动不动,仿佛被钉在了原地。餐馆经理最先反应过来,冲过来扶起杨澈。
"快叫救护车!快!"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夜空。在去往医院的路上,
杨澈的眼睛被紧急处理过,但仍然火辣辣地疼。他躺在担架上,
身体因疼痛和恐惧而不断颤抖。"会没事的,一定会没事的..."安雪坐在救护车角落,
声音细如蚊呐。她跟着来了医院,尽管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做。急诊室的灯光刺眼得令人眩晕。
医生迅速检查了杨澈的情况,表情越来越凝重。"热汤造成了角膜严重损伤,
"医生最终宣布,"需要立即手术,但...情况不太乐观。""什么意思?
"杨澈的声音嘶哑,双手死死抓住病床边缘。医生叹了口气:"杨先生,您要做好心理准备。
您的视力可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,最坏的情况是...失明。"这个词像一把锋利的刀,
直接刺入杨澈的心脏。失明?对于一个画家来说,失明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他再也看不见色彩,看不见线条,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。
意味着他精心准备的画展,他引以为傲的才华,他规划好的未来,全部化为泡影。
"不...这不可能..."杨澈摇着头,声音里充满了不可置信,"三天后我有画展,
我还有很多作品没完成...我不能失明..."他的声音逐渐升高,
最后变成了歇斯底里的怒吼:"我不能失明!你们必须治好我!必须!
"医护人员试图安抚他,但杨澈已经完全失控。就在这时,
他的"视线"——如果那模糊扭曲的光影还能被称为视线的话——捕捉到了站在角落的安雪。
"是你!"杨澈猛地指向她,尽管他其实看不清她的位置,"都是你的错!
你知道眼睛对我有多重要吗?你知道我为了这次画展付出了多少吗?现在全毁了!全毁了!
"安雪缩在墙角,眼泪无声地流下。她想说对不起,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
发不出声音。"滚出去!"杨澈抓起床头的水杯朝声音方向砸去,杯子在安雪脚边碎裂,
"我不想看见你!永远不想!"安雪颤抖着蹲下身,一片一片捡起玻璃碎片,
仿佛这是她唯一能做的赎罪方式。她的手指被划破,鲜血滴落在医院洁白的地板上,
但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。"杨先生,请您冷静。"医生按住激动的杨澈,
"我们需要立即为您安排手术,越早治疗,希望越大。"杨澈终于安静下来,
但全身仍在发抖。在被推进手术室前,
他最后听到的是安雪微弱但坚定的声音:"我会负责的...不管发生什么,
我都会负责到底..."手术室的灯亮了,又灭了。当杨澈再次"醒来"时,
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永恒的黑暗。2杨澈用指尖触摸着病房的墙壁,一步一步向前挪动。
出院已经三天了,他的世界依然是一片浓稠的黑暗。医生说他还有微弱的光感,但对他来说,
这与完全失明无异。"小心,这里有台阶。"安雪的声音从身侧传来,
她的手虚扶在杨澈肘边,既不敢真的触碰他,又怕他摔倒。"我知道!"杨澈猛地甩开手臂,
"不用你假好心。"他的动作太大,失去平衡向后踉跄了一步。安雪赶紧上前扶住他,
却被他狠狠推开。"别碰我!"杨澈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,"如果不是你,
我根本不会变成这样!"安雪沉默地退开半步,手指绞在一起。
这是杨澈出院后她接他回家的第一天,也是她正式搬进他公寓照顾他的开始。
过去一个月在医院,有护士和医生在,杨澈的怒火还算克制。但现在,
这个封闭的公寓里只有他们两个人,所有的愤怒和绝望都无处遁形。杨澈摸索着向前走,
膝盖撞在了茶几上。疼痛让他倒抽一口冷气,更加怒不可遏。"你把家具都挪到哪里去了?
"他吼道,"原来根本不是这个位置!""对不起..."安雪小声说,
"我想着把通道清出来,方便你行走...""方便我?"杨澈冷笑,
"你是为了方便看我的笑话吧?一个瞎子在自己家里跌跌撞撞,多有趣啊!
"安雪的呼吸变得急促,但她说不出反驳的话。她只是默默上前,扶住杨澈的手臂,
这次没有被他甩开。"沙发在你右手边,"她轻声说,"再往前两步就是。
"杨澈僵硬地坐下,手指深深陷入沙发垫中。这个公寓他住了两年,每一寸空间都了如指掌。
曾经,他能在黑暗中准确摸到每一件物品——画架在窗边,颜料柜在墙角,
咖啡机在厨房左侧台面。现在,这些熟悉的东西都变得陌生而危险。"我去准备午饭。
"安雪说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杨澈听到她走进厨房,打开冰箱,锅碗轻轻碰撞的声音。
他仰头靠在沙发上,突然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绝望。三天前,医生告诉他,
找到合适角膜的几率很小,可能要等待数年。数年...他的画展,他的毕业设计,
他刚接到的商业合作,全都化为泡影。"吃饭了。"安雪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。
杨澈闻到了饭菜的香气,但他拒绝表现出任何兴趣。他慢慢挪到餐桌前,
故意不按安雪指引的位置坐下,结果撞到了椅子边缘。"嘶——"疼痛让他更加烦躁。
"您的筷子..."安雪将筷子放在他手边。杨澈突然抬手,将整碗热汤打翻在桌面上。
汤汁四溅,有些甚至溅到了安雪的衣服上。"太烫了!"他厉声说,"你想再烫伤我一次吗?
"安雪站在原地,汤水从桌沿滴落到她的帆布鞋上。她没有擦拭,
只是轻声说:"我再去盛一碗。""不必了!"杨澈站起身,故意踢翻了椅子,"我不吃了。
"他摸索着向卧室走去,途中故意撞倒了立在墙边的画架。金属框架砸在地板上发出巨响,
他听到安雪倒吸一口气——那是他曾经最珍视的画架,法国进口,价值不菲。
杨澈心里涌起一阵扭曲的快感。对,就是这样,毁掉一切,就像她毁掉我一样。
他重重关上卧室门,倒在床上。门外传来安雪轻轻收拾残局的声音,扫把划过地板,
抹布擦拭桌面...这些细微的声响不知为何让他更加烦躁。不知过了多久,
杨澈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站在画展现场,所有人都在赞美他的作品。
突然,画面扭曲,所有的画作都变成了空白,人群开始指着他嘲笑...杨澈猛地惊醒,
额头渗出冷汗。房间里一片漆黑——现在对他来说,醒着和睡着已经没有视觉上的区别了。
他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,伸手摸去,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碗还温热的粥和几样小菜。
他犹豫了一下,最终还是拿起勺子。粥的温度刚好,咸淡适中,小菜是他喜欢的口味。
杨澈吃得很快,他确实饿了。吃完后,他将碗重重放回床头柜,故意弄出很大声响,
表示自己并不领情。清晨,杨澈被一阵轻微的响动吵醒。他听到安雪在客厅走动的声音,
还有...铅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?她在干什么?杨澈悄悄下床,扶着墙走到卧室门边。
他轻轻推开门,听到安雪立刻停下了动作。"您醒了?"她的声音有些慌张,
"我...我在整理房间。"杨澈冷笑一声:"是吗?那刚才是什么声音?
""我...我在记一些东西,购物清单..."安雪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杨澈没有追问,
但他记住了这个异常。早餐时,他又开始新一轮的刁难——抱怨面包太硬,果酱太甜,
咖啡太苦...安雪一一应下,承诺下次改进。上午,杨澈的朋友林昊来拜访。听到门铃声,
安雪去开门。"你是谁?"林昊的声音充满警惕。
"我...我是..."安雪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"她是那个害我失明的服务员。
"杨澈从沙发上站起来,语气讥讽。林昊恍然大悟,随即态度变得尖锐:"哦,
就是那个'泼汤高手'啊!怎么,现在是来赎罪的?"安雪低着头,默默退到厨房。"兄弟,
你怎么能让这种人待在你家?"林昊压低声音,"谁知道她安的什么心?"杨澈没有回答。
他听到厨房里安雪轻轻洗杯子的声音,水流的节奏很稳,没有因为林昊的话而产生波动。
"我带了点东西给你。"林昊转移了话题,"你之前参与的那个商业项目,
公司决定...终止合作了。他们等不了那么久..."杨澈的手指攥紧了沙发扶手。
那个项目是他花了三个月心血准备的,一旦成功,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公司核心设计团队。
"王教授让我转告你,学校会保留你的学籍,但画展..."林昊欲言又止。"取消了,
是吧?"杨澈的声音异常平静。"嗯...他们说要换成张明远的作品。"林昊叹了口气,
"那家伙一直嫉妒你,现在可得意了。"杨澈突然感到一阵眩晕。张明远,
那个永远的第二名,现在要取代他的位置,用他的展厅,享受本应属于他的荣耀。"滚出去。
"杨澈说。"什么?""我说,滚出去!"杨澈猛地站起来,撞翻了茶几上的果盘,
"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完蛋是吧?现在你们满意了?
"林昊被这突如其来的爆发惊呆了:"杨澈,我不是这个意思...""出去!全都出去!
"杨澈抓起手边能摸到的任何东西往地上砸,"包括你!"他朝厨房方向吼道,"都给我滚!
"林昊仓皇离开。安雪从厨房走出来,蹲下身开始收拾地上的碎片。"我叫你滚没听见吗?
"杨澈喘着粗气说。安雪没有回答,只是继续默默地捡着玻璃碎片。突然,
杨澈听到她轻轻倒吸一口气——大概是割到手了。"活该。"杨澈说,
但语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强硬。他摸索着回到卧室,重重关上门。门外,
安雪依然在收拾残局,动作很轻,像是怕再次惊动他。夜深了,杨澈躺在床上无法入睡。
他听到客厅传来细微的声响,像是铅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。安雪到底在干什么?
这个疑问在他心头盘旋。悄悄下床,杨澈摸索着来到门边,轻轻推开一条缝。
铅笔的声音立刻停止了,取而代之的是安雪急促的呼吸声。"您...您需要什么吗?
"她问,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慌乱。杨澈没有回答。他关上门,回到床上,
但那个疑问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生根发芽。第二天早晨,杨澈故意起得很早。
他听到安雪在厨房准备早餐,便悄悄摸到客厅。
昨晚她坐的位置是沙发左侧...杨澈摸索着,在沙发垫缝隙间找到了一张折叠的纸。
他刚把纸藏进口袋,就听到安雪的脚步声靠近。"您怎么起来了?"她问,
"早餐还没准备好...""上厕所。"杨澈生硬地回答,迅速回到卧室。关上门,
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,用手指仔细触摸。纸上有些凹凸不平的痕迹,像是铅笔留下的线条。
杨澈试图"阅读"这些痕迹,但失明后的触觉还不足以让他辨认出具体内容。这到底是什么?
安雪为什么要偷偷画东西?一个个疑问在杨澈脑海中盘旋,但他决定暂时按兵不动。
无论她在计划什么,他都会找机会揭穿她。早餐时,杨澈的态度反常地平静。
他没有挑剔食物,甚至说了声"谢谢"。安雪显然注意到了这个变化,
她的动作变得更加小心翼翼,仿佛在等待另一只靴子落地。"今天天气很好,"安雪轻声说,
"要...要去阳台透透气吗?"杨澈本想拒绝,但封闭的公寓确实让他感到窒息。
他点了点头,任由安雪引导他来到阳台。微风拂过脸颊,带着初秋的清爽。阳光照在皮肤上,
暖融融的。杨澈突然意识到,这是他失明后第一次感受到阳光。
"医生说...适当的光感刺激对您的情况可能有帮助。"安雪站在一旁说。杨澈没有回应。
他沉浸在这久违的温暖中,有那么一瞬间,忘记了愤怒。但很快,
现实又回来了——他能感受到阳光,却再也看不见它灿烂的模样。"回去吧。"他转身说,
语气重新变得冰冷。安雪轻轻叹了口气,扶着他回到客厅。杨澈敏锐地注意到,
她的手上贴着创可贴——是昨晚收拾玻璃碎片时割伤的吗?这个念头刚冒出来,
杨澈就强行将它压了下去。他不该在意这些,不该对她产生任何同情。是她毁了他的一切,
这点小伤算什么?午饭时,杨澈又开始新一轮的刁难。他把饭菜搅得乱七八糟,
抱怨味道太咸,最后干脆把整盘菜掀翻在地。"重做!"他命令道。安雪没有说话,
只是蹲下身收拾地上的食物。杨澈听到她轻微的抽泣声,但当他仔细听时,
又只剩下平静的呼吸声。下午,
杨澈坐在沙发上"听"电视——这是他现在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方式。安雪在厨房忙碌,
偶尔出来为他添茶。每当她靠近,
杨澈都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——她大概一直在打扫卫生,
试图让这个公寓保持一尘不染。傍晚时分,门铃响了。安雪去开门,
杨澈听到一个陌生的男声。"安小姐,
关于您母亲的医疗费..."安雪急忙打断对方:"我们出去说。"然后迅速关上了门。
杨澈挑了挑眉。母亲的医疗费?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信息。几分钟后,安雪回来了,
脚步沉重。"谁?"杨澈直截了当地问。"没...没什么,推销的。"安雪明显在撒谎。
杨澈冷笑一声,但没有追问。又一个谜团,安雪似乎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夜深人静时,
杨澈再次听到那微弱的铅笔声。这次他没有起身,只是在黑暗中睁着无神的眼睛,
思考着这个闯入他生活的女孩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。报复的快感正在消退,
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情绪。每当他羞辱安雪后,看到她默默承受的样子,
心里就会涌起一丝不适。特别是今天知道她可能还有生病的母亲要照顾后..."不,
"杨澈喃喃自语,"我不该心软。"他翻了个身,强迫自己入睡。明天,
他会有新的方式让安雪付出代价。至少,他是这么告诉自己的。3凌晨三点十七分。
杨澈盯着眼前的黑暗,数字时钟的报时声刚刚响过。自从失明后,他的睡眠变得支离破碎,
常常在深夜醒来,然后盯着永恒的黑暗直到天明。他翻了个身,
床单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卧室里格外清晰。就在这时,
一阵细微的、有节奏的沙沙声从客厅传来。又是那个声音。过去一周,
杨澈几乎每个深夜都能听到这个声音——铅笔在纸上划动的声响,轻得像是怕被人发现,
却又持续不断。安雪到底在干什么?杨澈轻轻坐起身,双脚触到冰凉的地板。
他摸索着找到放在床边的盲杖,但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。盲杖会发出声音,他不想惊动安雪。
扶着墙壁,杨澈悄无声息地向卧室门移动。他的动作比刚失明时灵活多了,
已经能记住公寓里大部分家具的位置。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,他屏住呼吸,
但铅笔的声音没有停止。客厅里只开了一盏小灯,杨澈能感觉到微弱的光感变化。
他站在走廊阴影处,朝向沙发的方向"望"去。
沙沙沙...沙沙沙...铅笔在纸上划动的节奏很稳,偶尔停顿,
然后是橡皮擦的细微摩擦声。安雪的呼吸很轻,但杨澈能听出其中的专注。"你在干什么?
"杨澈的声音突然划破寂静,铅笔声戛然而止。他听到安雪倒吸一口气,纸张翻动的窸窣声,
椅子向后推的刺耳声响。"我...我..."安雪的声音里满是慌乱,
"我只是在记一些东西...""半夜三点?"杨澈冷笑一声,朝声音方向走去,
"给我看看。""不,这没什么重要的..."安雪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杨澈已经走到沙发前,
伸出手:"给我。"一阵沉默后,一张纸被塞进他手里。杨澈用手指仔细触摸纸面,
凹凸不平的铅笔痕迹形成某种图案,但他无法辨认具体内容。"这是什么?"他皱眉问道。
"是...是您的一幅设计稿。"安雪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,
"《破晓》系列的最后一幅..."杨澈的手指僵住了。《破晓》是他为即将——不,
是本来应该即将举办的个展准备的系列作品,描绘光与暗的交界处。
最后一幅《破晓Ⅶ》他还没来得及完成就..."你偷看我的作品?
"杨澈的声音危险地低沉下来。"不是的!"安雪急忙解释,
"您之前把画稿放在书房的抽屉里,我是...我是想...""想怎样?替我完成?
"杨澈突然提高音量,"你以为你是谁?一个连盘子都端不稳的服务员,也配碰我的作品?
"纸张在他手中颤抖,杨澈突然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愤怒。他三下两下将纸撕得粉碎,
碎片像雪花一样飘落在地板上。"滚回你的房间去!"他吼道,
"别再让我发现你碰我的东西!"安雪没有出声,但杨澈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和轻微的抽泣。
脚步声快速远去,次卧的门轻轻关上,锁舌发出咔哒一声轻响。杨澈站在原地,
胸口剧烈起伏。他蹲下身,摸索着捡起地上的纸片,指尖触到湿润的痕迹——是眼泪。
安雪哭了?这个认知让杨澈心里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,但他很快压下了它。她活该,
谁让她擅自碰他的作品?回到床上,杨澈辗转反侧。为什么安雪要临摹他的画?是出于愧疚?
还是...不,不可能有别的理由。他强迫自己入睡,
但那些被撕碎的纸片和上面的泪痕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清晨,杨澈被电话铃声惊醒。
他摸索着接起床头柜上的手机。"杨澈?我是李总。
"电话那头传来他兼职设计公司老板的声音。杨澈立刻清醒了几分:"李总,早上好。
""关于你负责的蓝天项目..."李总的声音有些犹豫,"公司决定让林昊接手了。
你知道的,客户等不了那么久..."杨澈的手指攥紧了被单:"我理解。""别误会,
公司还是很看重你的才华。"李总赶紧补充,"等你...等你的情况好转了,
随时欢迎回来。""谢谢。"杨澈机械地回答,挂断了电话。
蓝天项目是他花了两个月心血准备的重要案子,一旦成功,毕业后就能直接成为公司合伙人。
现在,一切都没了。杨澈坐在床边,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绝望。失明已经一个多月了,
医生说过找到合适角膜的几率很小,可能要等上好几年。几年后,谁还会记得杨澈这个名字?
设计行业更新换代那么快,等他重见光明,早就被淘汰了。"您醒了吗?"安雪轻轻敲门,
"早餐准备好了。"杨澈没有回答。他听到门被小心地推开,安雪轻手轻脚地走进来,
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。"李总来电话了?"她小心翼翼地问。
杨澈猛地抬头:"你偷听我电话?""不,
我只是...路过时听到了一点..."安雪急忙解释,"是关于项目的事吗?
""关你什么事?"杨澈冷笑,"怎么,现在连我的工作也要插手了?"安雪沉默了一会儿,
然后轻声说:"我只是想帮忙...""帮忙?"杨澈的声音充满讥讽,"你能帮什么忙?
替我画设计稿?替我见客户?还是替我看这个该死的世界?"安雪没有回答。
杨澈听到她深吸一口气,然后脚步声慢慢远去。门关上后,
他抓起托盘上的杯子狠狠砸向墙壁,玻璃碎裂的声音让他有种扭曲的快感。早餐他一口没动。
上午,杨澈独自坐在阳台上,任凭初秋的风吹乱他的头发。失明后,时间变得模糊而漫长,
每一天都像是一场煎熬。中午时分,门铃响了。杨澈听到安雪去开门,
然后是压低声音的交谈。
"这次价格低了点...但你是老客户了..."一个陌生的男声说道。"没关系,抽吧。
"安雪的声音很轻。抽?抽什么?杨澈皱眉,悄悄向门口移动。"你脸色不太好,
确定今天要继续?"陌生男人问。"我没事...请快一点,
别让他发现..."杨澈的心突然跳得很快。他猛地推开通往客厅的门:"安雪!
"交谈声立刻停止,然后是慌乱的脚步声和门关上的声音。"是谁?"杨澈质问道。
"没...没有人,是送快递的..."安雪明显在撒谎。杨澈大步向前,突然脚下一滑,
差点摔倒。他摸到地上有几滴温热的液体——是血?"你做了什么?"他的声音变得危险。
安雪没有回答。杨澈循着她的呼吸声走去,一把抓住她的手腕。安雪轻呼一声,
杨澈摸到她肘弯处贴着什么东西——是医用胶带?"你卖血?"杨澈震惊地问。
安雪的手腕在他掌心里微微发抖:"我...我需要钱...""为了什么?"杨澈逼问,
"我并没有要求你赔偿。""不是为了赔偿..."安雪的声音几乎听不见,
"医院说...如果有合适的角膜...需要预付一部分费用..."杨澈松开了手,
像是被烫到一样。安雪在为他筹角膜移植的钱?通过卖血?
"装什么圣人..."他冷笑一声,但语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强硬,"我不需要你的钱。
""我知道您看不上这点钱..."安雪轻声说,"但我想尽一份力..."杨澈转身走开,
不想让她听到自己声音里的动摇:"别再做这种事了,让人恶心。"整个下午,
杨澈都沉浸在这个新发现中。安雪卖血是为了给他筹手术费?为什么?出于愧疚?
还是...他摇摇头,不愿再想下去。晚饭时,杨澈反常地安静。他没有挑剔食物,
甚至说了句"味道不错"。安雪似乎很惊讶,刀叉不小心碰到盘子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"谢谢..."她小声回应。饭后,杨澈坐在沙发上"听"电视。安雪在厨房洗碗,
水流声和碗碟碰撞的声音构成一种奇异的安宁感。突然,一阵闷响从厨房传来,
然后是安雪压抑的痛呼。杨澈立刻站起来:"怎么了?
""没事...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..."安雪的声音有些虚弱。杨澈犹豫了一下,
还是向厨房走去。他闻到一丝血腥味:"你受伤了?""只是小割伤..."安雪说,
但杨澈听出她在强忍疼痛。他伸出手:"让我看看。"安雪的手腕被轻轻放入他掌心。
杨澈摸到一道细长的伤口,湿漉漉的——还在流血。他的指尖触到她的皮肤,冰凉得不像话。
"你需要包扎。"杨澈说,语气比自己预想的要柔和。
"没关系...我习惯了..."安雪想抽回手。杨澈没有松开:"医药箱在哪里?
""客厅柜子第二层..."杨澈摸索着找到医药箱,取出纱布和消毒水。
他小心地为安雪清理伤口,动作出乎意料地熟练——艺术家对手的控制总是很精准。
"您...您不用这样的..."安雪的声音有些颤抖。"闭嘴。"杨澈说,
但手上动作依然轻柔。包扎完毕,他注意到安雪的手腕细得惊人,骨头凸出,
仿佛一用力就会折断。她最近瘦了很多吗?"你去休息吧。"杨澈突然说,"碗明天再洗。
"安雪似乎愣住了:"可是...""我说了,去休息。"杨澈转身离开厨房,
不想让她看到自己脸上的表情。夜深了,杨澈躺在床上,却无法入睡。
他想起那些被自己撕碎的画纸,想起安雪卖血的事,
想起她纤细的手腕...这些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浴室传来水声,安雪在洗漱。
水声停止后,杨澈听到一声压抑的啜泣,然后是极力克制的抽泣声。安雪在哭,
而且努力不让他听见。这个认知让杨澈胸口发紧。
他从未想过安雪会在独处时哭泣——在他面前,她总是那么隐忍,那么坚强,
承受他所有的怒火而不发一言。现在她哭了,因为什么?因为他的刻薄?因为卖血的痛苦?
还是因为看不到希望的前景?杨澈翻身下床,无声地走到浴室门外。他的手举起来,
想要敲门,却在最后一刻停住了。他能说什么?道歉?安慰?都不合适。最终,
他默默回到床上,但安雪的哭声却留在了他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第二天早晨,
杨澈起得很早。他摸索着来到客厅,
朝着沙发方向走去——那是昨晚安雪偷偷画设计稿的地方。他蹲下身,在地板上摸索,
终于找到了那些被撕碎的纸片。一片一片,杨澈将它们收集起来,放在茶几上。
他的手指仔细触摸每一片纸上的铅笔痕迹,试图在脑海中重建那幅画的样子。
安雪临摹的是《破晓Ⅶ》,那个他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作品...她画得怎么样?
有没有抓住精髓?这个念头让杨澈自嘲地笑了。
他居然在期待一个餐馆服务员能理解他的艺术?但内心深处,
有个小小的声音在问:如果她真的理解呢?"您...您在干什么?
"安雪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杨澈猛地停下手上的动作。他没想到她会这么早起床。"没什么。
"他迅速站起身,纸片从指间滑落。安雪走近,
听到她捡起那些纸片的声音:"对不起...我不该擅自碰您的作品..."杨澈没有回答。
他转身向阳台走去,需要新鲜空气来理清思绪。早餐时,杨澈注意到安雪的动作比平时更轻,
仿佛在极力避免发出任何声音。她的手腕上还缠着他昨晚包扎的纱布,看上去苍白而脆弱。
"今天..."杨澈突然开口,又停顿了一下,"今天天气怎么样?
"安雪似乎很惊讶他会问这个:"晴...晴天,有些云。""推我去阳台坐坐吧。
"杨澈说,语气不再那么尖锐。安雪小心翼翼地扶他来到阳台,
调整好轮椅的位置——这是杨澈失明后第一次同意使用轮椅。阳光照在脸上,温暖而舒适。
杨澈仰起头,让阳光洒满整个脸庞。他能"看到"一片橙红色的光晕,那是他仅剩的光感。
"《破晓Ⅶ》..."杨澈突然说,"你临摹的那幅,画的是什么?"安雪沉默了一会儿,
仿佛在思考该如何回答:"是...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,背对着观众,面对初升的太阳。
他的脚下是黑暗,但前方...全是光。"杨澈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安雪准确地描述了他脑海中的画面,
甚至捕捉到了他想要表达的情感——站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,渴望触碰光却又被黑暗束缚。
"你学过画画?"他问,声音不自觉地柔和下来。"一点点...在高中时。
"安雪轻声回答,"只是业余爱好..."杨澈没有再说话。他坐在阳光下,
第一次感到内心那股熊熊燃烧的怒火似乎减弱了一些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平静。也许,
只是也许,安雪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粗心大意的服务员。也许,在她安静的外表下,
藏着更多他未曾发现的东西。这个念头让杨澈既不安又莫名地期待。
4杨澈的手指在钢琴键上悬停,迟迟没有落下。自从失明后,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弹琴。
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他的手背上,温暖而明亮——至少医生说他应该多接触阳光,
这对仅存的光感有好处。"您会弹钢琴?"安雪的声音从厨房门口传来,
带着掩饰不住的惊讶。杨澈收回手:"以前会。"他没有说那是他十二岁前的事,
在父亲离家出走后,家里再也负担不起钢琴课的费用。
这台电子钢琴是大学时用第一笔设计奖金买的,原本打算重拾儿时的爱好,
现在却成了又一件无用的摆设。"您想弹什么曲子?"安雪走近,
杨澈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洗洁精味道,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——自从发现她卖血后,
他总是能闻到这种气味。"《月光》。"杨澈不假思索地回答,随即自嘲地笑了,"算了,
反正我也看不见琴键。""我可以帮您。"安雪的声音很轻,像是怕被拒绝,
"我...我学过一点。"杨澈挑眉:"你?""嗯,小时候妈妈是钢琴老师。
"安雪的声音里有一丝怀念,
"虽然家里没钱让我学太久..."杨澈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
突然说:"坐过来。"安雪小心翼翼地在他身边坐下,杨澈能感觉到沙发凹陷的弧度。
她身上那股淡淡的血腥味更明显了。"手。"杨澈命令道。安雪迟疑地将手放在琴键上,
杨澈摸索着找到她的手腕,将她的手指摆到正确的位置。"这是C大调的音阶。
"他引导着她的手指,"《月光》的第一小节从这里开始。
"安雪的手指在他的引导下按下琴键,清澈的音符流淌而出。杨澈松开手,让她自己尝试。
起初几个音符磕磕绊绊,但很快,安雪找到了感觉,旋律渐渐连贯起来。
杨澈闭上眼睛——虽然对他来说开闭眼已经没有区别——让音乐包围自己。
安雪的演奏并不完美,但有种质朴的情感,让他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时的震撼。
"你弹得很好。"曲子结束后,杨澈不情愿地承认。
安雪的呼吸明显加快了:"谢谢...是您教得好。"杨澈突然意识到两人的距离有多近。
他能感觉到安雪身体散发出的热量,听到她轻微的呼吸声。这个认知让他不自在起来,
他站起身,故意撞到了茶几。"我去倒水。"他生硬地说,摸索着向厨房走去。身后,
安雪没有出声,但他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追随着自己。最近几天,
杨澈注意到安雪看他的次数变多了——当然,他看不见,但他能感觉到那种注视的重量。
厨房里,杨澈打开水龙头,让冷水冲刷自己的手指。
他不明白为什么刚才那一刻会让他如此不安。是因为安雪弹出了他无法再弹奏的曲子?
还是因为她在黑暗中展现出的那种坚韧?手机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杨澈摸索着接起电话。
"杨先生?我是市立医院眼科的张医生。"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熟悉,"有个好消息,
我们找到了一个可能匹配的角膜供体。"杨澈的手指猛地收紧,几乎捏碎手机:"什么?
""初步配型很成功,如果您决定接受移植,需要尽快办理手续并预付部分费用。
"医生停顿了一下,"大约需要十五万。"十五万。这个数字像一盆冷水浇在杨澈头上。
他的存款加上保险赔付也只有八万左右,剩下的..."我...我会尽快给您答复。
"杨澈挂断电话,站在原地,一时不知该如何消化这个消息。光明。他可能重见光明。
但七万的缺口从哪里来?向父母借?自从父亲离家后,母亲一个人勉强维持生计,
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朋友?林昊他们也只是学生..."您还好吗?
"安雪的声音从厨房门口传来。杨澈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呆站了很久。
他深吸一口气:"医院找到了角膜。"安雪倒吸一口气:"真的?那...那太好了!
什么时候手术?""钱不够。"杨澈直截了当地说,"还差七万。"一阵沉默。
然后安雪轻声说:"我...我可以借给您。"杨澈冷笑:"用你卖血的钱?
"安雪没有回答,但杨澈听到她的手指绞在一起的声音。"别开玩笑了。"杨澈推开她,
走向客厅,"我不会接受你的钱。""为什么?"安雪跟上来,
声音里有一丝杨澈从未听过的急切,"这是您重见光明的机会!""然后欠你一辈子人情?
"杨澈猛地转身,"我宁愿继续当瞎子!"安雪被他突然爆发的怒火震住了。
杨澈能感觉到她在颤抖,但她没有退缩:"不是人情...这是我应该做的。""应该?
"杨澈的声音危险地低沉,"因为那碗汤?听着,我不需要你的赎罪,不需要你的同情,
更不需要你卖血换来的钱!""不是同情!"安雪突然提高了声音,
这是她第一次对杨澈大声说话,"我只是...只是...""只是什么?"杨澈逼问。
安雪的声音又低了下去:"只是不想看您放弃希望..."杨澈愣住了。希望?
他已经放弃希望很久了。从医生宣布他可能永久失明的那一刻起,从画展被取消的那一刻起,
从公司终止合作的那一刻起...希望对他而言早已是奢侈品。"我去筹钱。"安雪突然说,
声音坚定,"给我三天时间。"杨澈想拒绝,想再次吼她别多管闲事,
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:"你怎么筹?""我有办法。"安雪没有正面回答,
"请您...请您一定要答应接受手术。"杨澈没有承诺。他听着安雪匆匆收拾东西的声音,
大门开合的声音,然后公寓陷入寂静。独自一人,杨澈站在客厅中央,
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。自从失明后,这是安雪第一次离开他这么久。
他摸索着走到沙发边坐下,手指无意识地抚过钢琴键,发出不和谐的声响。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