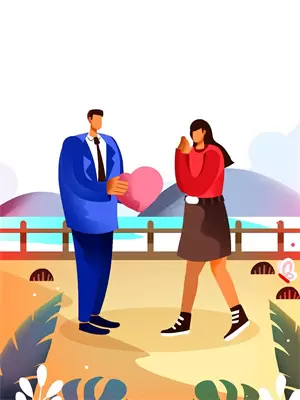第一章 生死时速"7.9级地震!缅甸克伦邦地区受灾严重,国际救援队急需外科医生!
"医院公告栏上的这行红字像一把刀,直接刺进我的眼球。我几乎是跑着回到办公室的,
白大褂下摆被风掀起,引来走廊上几个实习生的侧目。但我顾不上这些,
手指已经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着申请邮件。"苏医生,你真要去?"护士长李姐推门进来,
手里还拿着我刚签过字的手术确认单,"那边现在很危险,余震不断,而且通讯中断,
连具体伤亡情况都不清楚。"我抬头,手指停在发送键上方:"正因为这样才更需要医生。
我是创伤外科的,这种时候不去,学这行干什么?"发送键被按下的一刻,
我感觉心脏跳得厉害,但不是因为害怕。那种熟悉的、面对未知挑战的兴奋感又来了,
就像我第一次主刀时那样。三天后,我站在了缅甸克伦邦临时医疗点的废墟上。
眼前的景象比新闻里报道的还要惨烈——整片整片的房屋像被巨人踩碎的饼干,
扭曲的钢筋从混凝土中刺出,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某种说不清的焦糊味。"苏暖医生?
"一个皮肤黝黑的当地向导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确认我的身份,"跟我来,
医疗帐篷在那边。"我们穿过一片临时清理出来的小路,两旁是排队等待治疗的伤者。
有人手臂骨折,
简单用木板固定着;有人头上缠着渗血的绷带;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小女孩安静地坐在角落,
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,眼神空洞。"到了。
"向导指了指前方一顶印有红十字的大型帐篷,"负责人是陈医生,他会安排你的工作。
"我刚要道谢,地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。"余震!"有人用缅甸语大喊。我本能地蹲下,
护住头部。耳边传来尖叫和建筑物进一步坍塌的轰隆声。几秒钟后,震动停止,
但远处又传来新的求救声。"医生!快来人啊!这里有孕妇!"一个年轻男子用英语呼喊着,
声音里满是惊恐。我来不及去报到,抓起随身医疗包就朝声音方向跑去。绕过一堆瓦砾,
我看到一个亚洲面孔的高个男人正跪在地上,试图搬开一块水泥板。
他穿着沾满尘土的黑色T恤,手臂肌肉因为用力而绷紧,
脖子上挂着一台看起来价格不菲的相机。"我是医生!什么情况?"我跪到他旁边。他抬头,
我这才注意到他有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,
即使在尘土飞扬的混乱中也清晰如星:"孕妇被压在下面,还有意识,但说她快生了!
"我迅速评估现场:一块倾斜的水泥板形成了一个狭小的三角空间,
下面隐约可见一名孕妇的上半身,她痛苦地呻吟着,脸色惨白。"你叫什么?
"我一边从医疗包里取出听诊器一边问那男人。"陆远,战地记者。"他简短回答,
同时继续尝试撬动水泥板,"我路过这里准备拍摄救援情况,听到她的呼救。""苏暖,
外科医生。"我俯身检查孕妇情况,"女士,能听到我说话吗?"孕妇微弱地点点头,
用当地语言说了几句。陆远立即翻译:"她说羊水已经破了,孩子要出来了。
"我的心沉了下去。这种情况下分娩,母婴都极度危险。
我迅速检查了她的生命体征——脉搏快而弱,血压偏低,有早期休克的迹象。
"必须马上把她救出来,然后接生。"我对陆远说,"但这块水泥板不能随便移动,
可能会引起二次坍塌。"陆远皱眉环顾四周:"我去找人帮忙和拿工具,
你能先稳定她的情况吗?"我点头,已经开始准备静脉输液。陆远起身跑开,
动作敏捷得像只猎豹。"坚持住,"我用简单的英语配合手势安慰孕妇,
"我们会救你和宝宝。"五分钟后,陆远带着三个当地人和一些简易工具回来了。
他们用千斤顶和木棍小心地稳定水泥板结构,而我则持续监测孕妇状况。"再给我十分钟,
"陆远喘着气说,汗水顺着他的太阳穴流下,"我们就能安全移开这块板子了。
"但命运没给我们十分钟。孕妇突然抓住我的手腕,痛苦地尖叫起来——宫缩加剧,
孩子等不了了。"来不及了,"我做出决定,"必须在这里接生。
"陆远震惊地看着我:"在这?没有无菌环境,没有——""我知道风险!"我打断他,
"但如果不现在接生,母婴都可能死亡。我需要你帮忙。"他深吸一口气,
点头:"告诉我该做什么。"接下来的四十分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的时刻。
在狭小的废墟缝隙中,我指导陆远用消毒液清洁孕妇下身,同时准备紧急接生。
余震又来了两次,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暂停操作,护住孕妇和我们自己。"我看到头了!
"陆远突然说,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喜。"好,现在听我指挥,"我保持冷静,
"当下次宫缩来临时,让她用力,你轻轻托住婴儿头部,
注意不要拉扯..."在尘土飞扬的废墟下,一个新生命艰难地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当婴儿微弱的啼哭声响起时,我发现自己和陆远的手不知何时紧紧握在了一起。"是个女孩,
"陆远轻声说,小心翼翼地把婴儿包裹在我准备的干净毛巾里,"她真小。
"我迅速处理脐带,检查新生儿状况。虽然早产,但生命体征还算稳定。
此时救援队终于赶到,用专业设备安全移开了水泥板,将母婴送往医疗帐篷。
当担架被抬走时,孕妇虚弱地伸出手抓住我和陆远,用缅甸语说了什么。
陆远翻译道:"她说谢谢我们给了她女儿生命。"我点点头,突然感到一阵疲惫袭来。
连续二十小时的飞行加上刚才的高强度救援,肾上腺素开始退去。"你还好吗?
"陆远扶住我摇晃的身体,"你需要休息。""还有很多伤员..."我试图站直。
"英雄也需要喘口气,"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块巧克力,"给,战地记者的秘密武器。
"我接过巧克力,意外发现是瑞士进口的高级货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,
这种小奢侈显得格外珍贵。"谢谢,"我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,甜味瞬间在舌尖绽放,
"没想到战地记者装备这么精良。"他笑了,
眼角挤出细纹:"习惯了在各种地狱里找点甜头。你刚才...很厉害。""职业本能而已。
"我耸耸肩,突然注意到他左臂有一道伤口,"你受伤了!"他低头看了看:"哦,
可能是搬东西时划的,小伤。""在这种环境下,任何伤口都不能忽视。"我严肃地说,
从医疗包里拿出消毒用品,"坐下,我给你处理。"他配合地坐下,我小心地清理伤口。
近距离看,我发现他比第一印象更英俊——高挺的鼻梁,线条分明的下颌,
还有那双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眼睛。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右眉上的一道旧伤疤,
给他原本精致的面容增添了几分粗犷。"这道疤也是战地记者的勋章?"我忍不住问。
"阿富汗,"他简短回答,然后转移话题,"你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救援吗?
""第一次地震救援,但不是第一次出国医疗援助。"我给他贴上敷料,
"去年在非洲待了三个月。"他正要说什么,远处又传来呼喊声:"医生!这边需要帮助!
"我们同时站起身。陆远捡起掉在地上的相机检查了一下:"还能用。要一起去看看吗,
苏医生?"我点头,把剩下的巧克力塞进口袋:"带路吧,战地记者。
"当我们跑向新的救援地点时,我莫名感到一种奇怪的安心——在这个陌生的国度,
在这样混乱的灾难中,我竟然因为一个刚认识不到两小时的男人而感到不那么孤单了。
---第二章 黑暗中的心跳"快让开!墙体要塌了!"我还没反应过来,
就被一股大力猛地拽向一旁。陆远的胸膛紧贴我的后背,他的手臂像铁箍一样环住我的肩膀。
下一秒,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伴随着地面剧烈震动,
我们刚才站立的地方已经被倒塌的墙体完全掩埋。"医疗帐篷!"我挣扎着要站起来,
灰尘呛得我直咳嗽。陆远的手稳稳地扶住我的腰:"慢点,余震可能还没结束。
"我抬头看向原本医疗帐篷的方向,
心一下子沉到谷底——那里现在只剩下一堆扭曲的金属支架和破碎的帆布。
医护人员和伤员们四散奔逃,哭喊声混着尘土在空气中弥漫。"苏暖医生?
"一个皮肤黝黑的当地向导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确认我的身份,"跟我来,
医疗帐篷在那边。"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持续到深夜。我和陆远辗转于各个废墟之间,
处理伤员、协助救援。他的缅甸语出奇地流利,
能够准确传达我的医疗指示;而我的急救知识也多次派上用场,
帮他处理那些他总说"小伤"的伤口。凌晨三点,我们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。
临时指挥中心搭起了一顶小帐篷,供救援人员轮流休息。我和陆远分到两个睡袋,
中间只隔着一臂的距离。"你睡吧,"陆远说,眼睛盯着帐篷外仍在进行的救援工作,
"我守一会儿。""你又不是我的保镖。"我钻进睡袋,却因为浑身酸痛而忍不住轻哼一声。
"疼?"他立刻转过头,眉头紧锁。"没事,只是肌肉抗议过度使用。"我试图轻松地说,
但声音里的疲惫出卖了我。他二话不说,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瓶子:"转过去。""什么?
""肌肉舒缓膏。转过去,我给你揉揉肩膀。"我犹豫了一下,但疼痛最终战胜了矜持。
转过身去,感觉他的手指隔着T恤落在我的肩膀上。力道恰到好处,既有力道又不会太痛。
"你怎么什么都有?"我舒服得几乎呻吟出声。"战地经验。"他的声音里带着笑意,
"在阿富汗学的,长时间扛相机导致肩膀劳损是职业病。
"他的手指找到了一个特别紧绷的结,轻轻按揉。我闭上眼睛,任由疲惫席卷全身。"陆远,
"我迷迷糊糊地问,"为什么当战地记者?"他的手指停顿了一秒,然后继续:"为了记住。
为了不让那些应该被记住的人和事被世界遗忘。"我想追问,但睡意如潮水般涌来。
在陷入黑暗前的最后一刻,我感觉到有人轻轻拉高了我的睡袋,
然后是一声几乎微不可闻的叹息。第二天清晨,我被一阵急促的哨声惊醒。
帐篷里已经没有了陆远的身影,但我的睡袋上放着一块新的巧克力和一张字条:"去东区了,
中午回来。别逞强。——陆"我忍不住微笑,把巧克力和字条一起塞进口袋。刚走出帐篷,
陈医生就匆匆走来:"苏医生!太好了你醒了!我们需要你去医院废墟,有幸存者!
"医院废墟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。七层的主楼完全坍塌,
据说下面埋着上百名医护人员和病人。我抓起医疗包就跑,一路上看到更多救援队正在集结。
到达现场时,情况比想象的更糟。废墟上尘土飞扬,救援人员正在小心地移开混凝土块。
一个狭窄的通道已经被清理出来,通向深处。"下面发现生命迹象,"救援队长说,
"但通道太窄,只有体型小的人能进去。我们需要医生确认伤者情况,再决定如何施救。
"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在场的救援人员大多身材魁梧,
而我165的身高和相对瘦小的体型成了优势。"我去。"我毫不犹豫地说。
戴上安全帽和头灯,我沿着通道小心前进。混凝土碎块刮擦着我的手臂和背部,
灰尘让我不断眨眼。头灯的光线在狭窄的空间里显得格外珍贵,照亮前方一小片区域。
"听到声音了吗?"领路的救援队员突然停下。我屏住呼吸,
隐约捕捉到微弱的敲击声从右前方传来。"这边!"他调整方向,小心地挪动。
又前进了约五米,通道突然变宽,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——可能是原医院的走廊。
敲击声更清晰了。"救命...我们在这里..."一个男声用英语喊着。
救援队员的头灯照到了三个身影,他们被困在一根倒塌的横梁和墙壁形成的三角空间内。
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,都灰头土脸但看起来没有严重外伤。
"医院的?"救援队员问,同时检查他们周围的结构。"是的,我是马克医生,
这是小林护士和吴先生,"男子回答,"地震时我们正在转移病人,
突然就...""能移动吗?"我蹲下来快速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。"可以,
但出口被堵住了,"叫小林的女性说,"我们试过..."她的话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打断。
碎石和灰尘从上方倾泻而下,救援队员猛地扑过来把我们护在身下。世界在摇晃、轰鸣,
仿佛末日降临。当震动停止时,我的心跳快得几乎要冲出胸腔。
救援队员迅速起身检查通道——完全被堵死了。"通讯器!"我摸向腰间的设备,
但只听到静电噪音。救援队员试了试他的,同样没有信号:"屏蔽太严重了。
"马克医生咳嗽了几声:"我们试过了,从里面根本联系不上外面。"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
用头灯检查四周。我们处在一个约四平方米的空间内,上方是交错的水泥板,
看起来暂时稳固,但谁知道下一次余震什么时候来。
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某种金属锈蚀的气味。"救援队知道我们的位置,"救援队员说,
声音异常平静,"他们会从外面挖掘。"小林蜷缩在角落里,
年轻的脸庞上满是恐惧:"但如果再来一次余震...""我们得保存体力和氧气,
"我打断她,医生的本能让我自动进入应急状态,"尽量少说话,放慢呼吸。
"救援队员点头赞同,开始分配我们有限的水和资源。
他把大部分水分给了两位医护人员和老人,只给自己和我留了一小口。
时间在黑暗中变得模糊。我们轮流休息,保持警觉等待救援。不知过了多久,
小林开始低声啜泣。"我们会死在这里,是不是?"她问,声音颤抖。"不会。
"救援队员斩钉截铁地说,"我经历过比这更糟的情况。""在哪儿?"马克医生问,
显然是为了分散小林的注意力。"阿富汗,"救援队员靠在墙上,头灯照向天花板,
"被塔利班困在一个地窖里三天,没有食物,只有半瓶水。
"我惊讶地看着他:"你是怎么活下来的?""挖地道,"他轻描淡写地说,"用一把勺子。
"小林停止了哭泣,好奇地问:"你为什么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?"救援队员沉默了一会儿,
然后说:"我妹妹死于地震。如果当时有更多现场报道,也许救援能更及时到达。
"我的心猛地一缩。在昏暗的光线中,我看到他脸上闪过一丝痛苦。"她在尼泊尔做志愿者,
"他继续说,声音低沉,"2015年那场大地震。"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
只能轻轻握住他的手臂。他看了我一眼,嘴角勉强扯出一个微笑。
"所以你成为战地记者是为了...""用我的方式完成她的心愿。"他看向轮椅上的老人,
"就像今天,如果没人来,这些人可能..."我没说话,只是握紧他的手。
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黑暗空间里,这个平日坚毅如钢铁的男人向我展示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。
天蒙蒙亮时,我们终于听到了上方传来的微弱的敲击声。救援队员立刻抓起一块碎石,
有节奏地敲击身旁的水泥板。片刻后,敲击声再次传来,这次更清晰了。"他们找到我们了!
"我激动地说,轻轻摇醒小林和马克医生。接下来的等待既漫长又短暂。敲击声越来越近,
偶尔还能听到模糊的人声。终于,一缕光线从上方透进来,接着是一个钻头突破了水泥板。
"在这里!我们在这里!"我们一起大喊。救援工作进行得很快。
他们先送下来水和氧气面罩,然后用液压顶撑开通道。
救援队员坚持让两位医护人员和老人先出去,然后是我,他最后一个离开。
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。当我终于适应光线时,看到的第一个人是陆远。他满脸尘土,
眼睛布满血丝,在看到我的瞬间亮了起来。"你!"他冲过来,双手抓住我的肩膀,
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,"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一整夜?!"我眨了眨眼,
被他罕见的情绪爆发震住了:"我...去救人...""下次!"他咬牙切齿地说,
"下次至少留个纸条!或者让人告诉我!或者——"他的话戛然而止,
突然一把将我拉进怀里。他的心跳快得吓人,透过胸膛传来,和我的一样。
"巧克力不管用了吗?"我轻声问,试图缓解气氛。他松开我,表情复杂:"这次不管用。
"救援队员最后一个被拉上来,看到陆远时明显愣了一下:"陆记者?你怎么在这里?
"陆远的表情瞬间变得警惕:"张队长?你不是在阿富汗吗?""上个月调回来的。
"被称为张队长的男人拍拍身上的尘土,然后看向我,"这位医生很勇敢,救了三条人命。
"陆远的目光在我和张队长之间来回扫视:"你们...认识?""在废墟下面,"我解释,
"张队长帮了大忙。"陆远的表情有些古怪,但很快恢复了平静:"走吧,你需要休息。
"他拉着我离开救援现场,力道比平时大了许多。我踉跄了一下,
他才如梦初醒般放松了手劲。"抱歉,"他低声说,"我只是...你消失了一整夜。
""我没事,"我轻声回答,"而且救了人,值得。"他深深看了我一眼,然后点头:"是,
值得。"我们沉默地走回临时营地。阳光越来越强,照在废墟上,
给这片灾难之地带来一丝不合时宜的温暖。我突然意识到,在这个陌生的国度,
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地方,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锚点——而这个锚点,
是一个带着瑞士巧克力和满身故事的战地记者。
第三章 暴雨中的心跳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,顺着冲锋衣的领口灌进去,
冰凉刺骨。
我眯着眼睛看向前方模糊的道路——原本就崎岖的山路在连续三小时的暴雨后变成了泥浆河。
"再坚持一下!前面就是村庄了!"陆远的声音在雨声中几乎听不清,他走在我前面,
高大的背影是我唯一的向导。三天前从废墟中获救后,医疗队决定分头行动,
向周边受灾更严重的村落运送药品。我和陆远被分到一组,前往这个位于山区的克伦族村寨。
原本六小时的路程,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,已经走了近九个小时。我的靴子陷进泥里,
差点摔倒。陆远立刻转身,一把抓住我的手臂。即使隔着雨衣,
我也能感受到他手掌的温度和力量。"谢谢,"我喘着气说,"我没事。
"他皱眉看了看我苍白的脸色,突然蹲下身:"上来,我背你。""别开玩笑了!"我摇头,
雨水流进我的眼睛,"你自己都走不稳。""苏暖,"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,
眼神出奇地认真,"我们已经损失了一个药箱,不能再损失一个医生。"我咬住嘴唇。
他说得对,一小时前我们过一条暴涨的溪流时,一个药箱被急流冲走了。
现在我们只剩下我背包里的紧急药品和他腰间的小型急救包。"我还能走,"最终我说,
"但如果我真的撑不住,会告诉你的。"他盯着我看了两秒,然后点头,
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塞进我手里:"吃了它。"那是一小块巧克力,包装纸已经湿透了,
但巧克力本身还完好。我惊讶地看着他:"你到底带了多少这个?""战地记者的秘密。
"他嘴角微微上扬,然后转身继续前进。巧克力在舌尖融化,
短暂的甜蜜让我恢复了些许力气。我跟上他的步伐,
心想这个男人的背包简直像哆啦A梦的口袋。雨势稍缓时,
我们终于看到了村子的轮廓——十几栋高脚屋散布在山坡上,大部分已经严重损坏。
最靠近山体的一栋完全被泥石流冲垮,只剩下几根歪斜的木桩。"情况比想象的还糟,
"陆远低声说,"希望伤亡不严重。"我们走近村子时,几个村民发现了我们,
大声呼喊着跑来。他们浑身湿透,脸上混合着雨水和泪水。一个中年男子抓住陆远的手臂,
急促地说着缅甸语。陆远的脸色越来越凝重,他转向我:"山体滑坡,
有三个孩子被困在那边。"他指向村子边缘一栋半倒塌的校舍,"他们去拿课本,
结果被堵在里面了。""带我去,"我立刻说,同时检查背包里的药品,"有人受伤吗?
""不确定,但情况很危险,随时可能再次滑坡。"陆远和村民快速交谈几句,然后对我说,
"你留在这里照顾其他伤员,我去救孩子。""不行!"我抓住他的雨衣,"太危险了!
等专业救援队...""来不及了,"他打断我,眼神坚定,"那栋建筑撑不了多久。
我是战地记者,记得吗?这种事我常干。"我还想反对,但看到他眼中的决心,
知道拦不住他。我迅速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型急救包塞进他口袋:"至少带上这个。还有,
用这个。"我递给他我的医用头灯,"比你的亮多了。"他愣了一下,然后接过,
手指轻轻擦过我的掌心:"等我回来。"看着他跟随村民冲向危险区域的背影,
我突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恐惧。这感觉太奇怪了——我和陆远认识还不到一周,
为什么他冒险会让我如此不安?"医生!医生!"一个老妇人拉我的袖子,
指向村子中央的大屋,"伤员在那里!"我强迫自己集中精神,跟着她走向临时安置点。
大屋里约有二十多人,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。角落里有三个简易担架,上面躺着伤者。
接下来的半小时,我全神贯注地处理伤员——一个腿部骨折的老人,
一个疑似肋骨骨折的妇女,还有一个高热惊厥的孩子。正当我给孩子的额头敷上湿毛巾时,
外面突然传来惊恐的喊叫声。我冲到门口,看到村民们指着山体方向。
远处传来低沉的轰隆声,像雷声,但持续不断。"又滑坡了!"有人用英语大喊。
我的心跳骤然停止——陆远还在那边!没有思考,我抓起剩下的药品冲出门外,
朝校舍方向奔去。雨又大了,打在我脸上像无数细小的针。泥浆没过脚踝,
每一步都像在铅液中跋涉。"陆远!"我声嘶力竭地喊着,声音淹没在雨声中。
绕过一片竹林后,我终于看到了那栋半倒塌的木结构校舍——或者说,它曾经的位置。
现在那里只有一堆被泥浆和碎石掩埋的废墟,新鲜的山泥还在不断从上方滑落。
"不..."我双腿发软,差点跪倒在泥浆里。就在这时,废墟边缘的木板突然动了一下。
我屏住呼吸,看到一只手从缝隙中伸出来,然后是第二只——抱着一个约五六岁的孩子!
"陆远!"我尖叫着冲向前。他艰难地从缝隙中爬出来,浑身是泥,怀里抱着昏迷的孩子。
接着又有一个稍大的男孩从他身后钻出,然后是第三个孩子,被一个当地青年抱着。"快跑!
"陆远吼道,"山体不稳!"我们跌跌撞撞地向安全地带撤退。陆远一手抱着孩子,
一手拽着我的手臂。刚跑出约五十米,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崩塌声——校舍完全被吞没了。
回到村子大屋后,陆远立刻将孩子平放在干净的地板上。孩子约六七岁,面色苍白,
嘴唇发紫,已经失去意识。"呼吸微弱,"我迅速检查,"可能是吸入性窒息。
"陆远跪在另一侧,已经开始进行心肺复苏。我们的手在孩子的胸口上方交错,
配合默契得像合作多年的搭档。"1,2,3..."我数着节奏,
看着他给小孩做人工呼吸。三分钟后,孩子突然咳嗽起来,吐出几口泥水,然后开始哭泣。
屋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。我瘫坐在地上,突然感到一阵眩晕——可能是紧张过后的反应,
也可能是过度疲劳。"苏暖?"陆远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我眨眨眼,
发现他正凑近看着我,满脸担忧。他的睫毛上还挂着泥水,右眉上的伤疤在油灯下格外明显。
"我没事,"我勉强笑笑,"只是...有点累。"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,
眉头皱得更紧了:"你在发烧。"我想反驳,但突然感到一阵恶寒袭来,
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。现在才意识到,我的衣服早已湿透,紧贴在身上,
冰冷得像第二层皮肤。陆远立刻脱下自己的外套——居然还相对干燥——裹在我肩上,
然后对村民说了几句缅甸语。一个老妇人点头,指向屋子后方的小房间。"他们有个储藏室,
我们可以暂时休息,"他低声说,"你需要换掉湿衣服和保暖。
""孩子们...""其他村民会照顾,"他打断我,"现在你是病人。
"储藏室狭小但干燥,堆满了麻袋和陶罐。陆远清出一小块空地,铺上几张干草席。
老妇人拿来两套简陋但干净的当地服装和几条毯子。"换上这个,
"陆远把其中一套衣服和一条毯子递给我,"我去外面等。""你也湿透了,"我没接,
"你先换。"我们僵持了一会儿,最后达成妥协——他转身面对墙壁,我先换上衣,
然后他换,再各自换裤子。整个过程尴尬得让我脸颊发烫,尽管我们之间隔着好几袋稻谷。
换好衣服后,我们并肩坐在草席上,裹着毯子。老妇人送来热茶和一些食物,虽然简单,
但对饥寒交迫的我们来说堪比盛宴。"你怎么知道校舍会塌?"我小声问,
双手捧着热茶汲取温暖。"经验,"他啜了一口茶,"阿富汗山区的泥石流我见过太多次。
那种声音...一旦听过就忘不掉。"我看着他疲惫的侧脸,
突然意识到这个看似坚强的男人经历过多少危险和伤痛。不是为了刺激,不是为了成名,
而是为了他妹妹...和更多像他妹妹一样的人。"三个孩子都安全了,"我说,
"你救了他们。"他摇摇头:"是我们救了他们。"顿了顿,又补充,"你不该跟来的,
太危险了。""彼此彼此,"我轻笑,"你冲进去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危险?""不一样,
这是我的工作。""救人是我的工作。"我们对视一眼,同时笑了起来。屋外暴雨依旧,
但这个小空间里却莫名温暖安全。我的手指因为寒冷仍然僵硬,茶杯在手中微微颤抖。
陆远注意到了,他放下自己的杯子,轻轻握住我的双手。他的手掌宽大温暖,
完全包裹住我的。"冷吗?"他低声问,拇指轻轻摩挲我的手背。我摇头,却说不出话来。
心跳声大得我怀疑他都能听见。在油灯昏黄的光线下,他的眼睛呈现出一种深邃的琥珀色,
像是能把人吸进去。"你的手像冰块,"他说,声音比平时低沉,然后将我的手拉到唇边,
轻轻呵气取暖。温热的气息拂过皮肤,我全身的神经末梢似乎都集中到了那一小块区域。
理智告诉我应该抽回手,但身体却不听使唤。就在这时,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。
我们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迅速分开。一个村民冲进来,神色慌张地对陆远说着什么。
"怎么了?"我问,一边把毯子裹得更紧。陆远的表情变得严肃:"刚才救的那个孩子,
开始抽搐发热。"我立刻站起来,眩晕感还没完全消退,但医生的本能已经接管了身体。
我们匆忙赶回主屋,看到那个小孩躺在母亲怀里,全身痉挛,眼睛上翻。"高热惊厥,
"我迅速判断,摸了摸孩子的额头——烫得吓人,"需要退烧药。"我打开药品包,
心沉了下去——大部分药品在另一个被冲走的箱子里,
剩下的退烧药刚才已经给另一个孩子用了。"没有退烧药了,"我咬着嘴唇说,
"只能用物理降温。"陆远已经端来一盆水和几条干净布。我们配合着给孩子擦身降温,
但效果有限。孩子的体温仍在上升,呼吸越来越急促。"这样不行,"我焦急地说,
"需要药物,否则可能脑损伤。"陆远沉思片刻,突然问村民:"村里有传统草药医生吗?
"经过一番交流,一个瘦小的老人被请来,手里拿着几株植物。他自信地说了几句,
开始准备某种煎剂。"他说这是他们世代用的退热药,"陆远翻译道,"比西药还灵。
"我犹豫了——未经科学验证的草药可能有风险,但眼下别无选择。"你相信他吗?
"我问陆远。他看了看老人,然后点头:"克伦族的草药学有几百年历史。在战地,
我见过比这更'原始'的方法救人命。"药煎好后,我小心地闻了闻——淡淡的苦味,
没有异常气味。孩子母亲信任地将药喂给孩子,我们则继续物理降温。约半小时后,
奇迹发生了——孩子的体温开始下降,呼吸也逐渐平稳。我长舒一口气,
这才发现自己的背已经被汗水湿透。"有效,"我难以置信地对陆远说,"居然真的有效。
"他微笑:"有时候最古老的智慧才是最珍贵的。"夜深了,大部分村民已经睡去,
只有我们和孩子的母亲还守着。孩子的状况稳定下来,但我不敢掉以轻心。
陆远坚持让我休息一会儿,由他来守夜。"你还在发烧,"他轻声说,
手指不经意地拂过我的额角,"睡吧,有情况我叫你。"我太累了,无法拒绝。
在陷入睡眠前的最后一刻,我感觉到一只有力的手臂轻轻环住我的肩膀,
让我靠在一个温暖坚实的躯体上。...模糊中,我听到陆远在说话,
声音低沉断续:"...不,
我不会回去...那些钱对我没有意义...我有我的选择..."我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,
看到陆远坐在门口,背对着我,似乎在自言自语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,
带着我从未听过的脆弱和固执。
像小妹一样...我必须做些什么..."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梦话或者发烧迷糊了。
正当我犹豫是否该"醒来"时,他转过头,看到我睁着眼,立刻停止了自言自语。
"吵醒你了?"他问,声音恢复了平常的沉稳。"你在发烧,"我坐起来,
伸手去摸他的额头——果然烫手,"该换我守夜了。"他摇摇头:"我没事。
刚才只是...""梦话?"我试探地问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苦笑:"算是吧。
""你提到了...你父亲?还有钱?"我小心地问。油灯的光线太暗,看不清他的表情,
但我感觉到他身体微微绷紧。"我家...很有钱,"他最终说,声音平静得不像在说自己,
"父亲是陆氏集团的董事长。"我瞪大眼睛——陆氏集团,亚洲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,
旗下产业遍布全球。"所以你是...""富二代?继承人?"他自嘲地笑了笑,"曾经是。
直到我放弃商学院,拿起相机。""因为你妹妹?"他点头,
眼神飘向远处:"小妹是家里的异类,从小就只想帮助别人。她去尼泊尔做志愿者,
父亲大发雷霆,断了她所有经济支持。我偷偷给她汇款,但..."他的声音哽住了。
我轻轻握住他的手,感受到他手指的轻微颤抖。"地震后,我飞到加德满都,
在废墟中找了七天七夜...最后只找到她的日记本。"他深吸一口气,
"里面写着她多么希望有人能告诉世界这里的灾情,让更多援助进来。
""所以你成了战地记者。""用我的方式完成她的心愿。"他看向睡着的孩子,
"就像今天,如果没人来,这些孩子可能..."我没说话,只是握紧他的手。
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雨夜,在这个简陋的高脚屋里,
这个平日坚毅如钢铁的男人向我展示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。天蒙蒙亮时,
孩子的状况突然恶化——他开始呼吸困难,嘴唇发紫。我迅速检查,发现肺部有啰音。
"可能是吸入性肺炎,"我焦急地说,"需要抗生素。"陆远立刻翻找药品包,
但我们都知道——最后的抗生素昨天已经用在一个伤口感染的老人身上了。
"最近的医疗站在哪里?"我问村民。"二十公里外,但路被泥石流切断了,
"陆远翻译他们的回答,脸色越来越凝重,"直升机也进不来,云层太厚。
"我看着孩子越来越弱的呼吸,心如刀绞。作为医生,
最痛苦的莫过于知道治疗方法却无法实施。"还有其他伤员需要抗生素吗?"陆远突然问。
我摇头:"只有他和昨天那个老人。""那老人的情况怎么样?""稳定了,
理论上可以减量..."我突然明白他的意思,瞪大眼睛,"不,我们不能拿走老人的药!
""如果不用,这孩子可能会死,"陆远直视我的眼睛,"而老人已经好转。
""这是违背医疗伦理的!"我压低声音,但语气激烈,"医生不能决定谁更值得救!
""这不是决定谁更值得救,"他也激动起来,"这是在有限资源下救活更多人!
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这样的选择!""这不是战场!""对这孩子来说,就是!
"我们剑拔弩张地对视着,周围的村民紧张地看着我们争吵。最终,
我深吸一口气:"我去看看老人的情况。"检查后确认老人的感染确实已经控制,
可以减量用药。我心情复杂地分出部分抗生素给孩子。药物起效很快,孩子的呼吸逐渐平稳。
"你没错,"陆远突然说,当我们站在屋外透气时,"医疗伦理很重要。
"我叹气:"你也没错。在这种极端条件下,有时候不得不做出妥协。"他看向远方的山峦,
雨终于停了,但天空依然阴沉:"这就是为什么我敬佩你们这些医生。每天面对这样的抉择,
还能保持初心。""也敬佩你们这些战地记者,"我轻声说,
"把世界的黑暗面展现给人们看,却还要保持希望。"我们对视一笑,
昨夜的争吵仿佛从未发生。就在这时,一个村民急匆匆跑来,指着村口方向说着什么。
"怎么了?"我问。陆远的表情变得警觉:"他们说听到奇怪的声音从山谷传来,
像是..."他的话被远处低沉的轰鸣声打断。那声音我昨天才听过——山体滑坡!
"所有人!"陆远用缅甸语大喊,"往高处撤!快!"混乱中,
他抓住我的手:"带上孩子和重伤员,快走!"当我们跌跌撞撞向山上爬去时,
我回头看了一眼——村子边缘已经开始被泥浆吞噬。而那个刚脱离危险的孩子,
突然在我怀里剧烈咳嗽起来,
渗出一丝鲜红的血...---第四章 血色晨曦那抹鲜红在孩子苍白的嘴角显得格外刺眼。
我的手指微微发抖,轻轻擦去血迹,心跳如擂鼓。"不是普通肺炎,"我抬头看向陆远,
声音绷紧,"可能是出血热类疾病。"陆远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,
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——传染病,在这样拥挤、卫生条件极差的临时避难所里,
一旦爆发就是灾难。"所有人后退!"他突然用缅甸语大喊,同时把孩子从我怀里接过去,
"这孩子需要隔离!"村民们惊恐地后退,
窃窃私语中我捕捉到几个重复的词——"瘟疫"、"死亡"。一个老人甚至开始画十字,
嘴里念着祷告词。"帮我找一块干净布,"我低声对陆远说,
同时迅速检查孩子的其他症状——高热持续、结膜充血、现在又有出血迹象,
"我需要做进一步检查。"陆远迅速撕下自己衬衫相对干净的下摆递给我。
我小心地擦拭孩子口鼻处的血迹,注意到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。"肺音很重,"我皱眉,
"需要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,但我们...""什么都没有,"陆远接话,声音低沉,
"最近的医疗站还有二十公里,路断了。"孩子的母亲在一旁啜泣,想要靠近又不敢。
我理解她的恐惧——在这样偏远的地方,传染病往往意味着死亡判决。
"不是所有出血热都高度传染,"我尽可能冷静地说,既是对陆远也是对村民,
"我们需要隔离患者,同时检查其他人是否有类似症状。"陆远迅速翻译我的话,
同时组织村民在较高处的平坦地带搭建简易隔离区。
他的领导才能在这种危机时刻展露无遗——短短半小时内,
几个用竹子和防水布搭起的隔离帐篷就建好了。"你懂传染病防控?"我有些惊讶地问。
"非洲埃博拉疫情时我在现场报道,"他简短回答,同时帮我把孩子转移到隔离帐篷,
"学了些基本知识。"帐篷内,我做了更详细的检查。孩子现在意识模糊,
皮肤出现细小的出血点,这是典型的毛细血管破裂迹象。"登革热?马尔堡?
还是..."我喃喃自语,额头渗出冷汗。没有检测设备,我甚至无法确定病原体类型。
"最坏情况是什么?"陆远跪在我对面,声音异常平静。"病毒性出血热,
死亡率可达50%以上,"我咬着嘴唇,"而且会通过体液传播。"帐篷外突然传来喧哗声。
陆远掀开帘子,我看到一群村民围在一起,情绪激动。一个中年男子正挥舞着火把,
指向隔离帐篷方向。"他们在说什么?"我问,尽管那愤怒的语调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陆远的嘴角绷紧:"他们认为应该...烧掉感染源。
"我的血液瞬间凝固:"他们想烧死孩子?""和所有接触过的人,"他的声音冷得像冰,
"包括我们。"恐惧像毒蛇一样爬上我的脊背。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,
恐慌往往比病毒杀人更快。几个壮年男子已经开始朝我们的帐篷走来,
手里拿着各种"武器"——锄头、木棍,甚至砍刀。陆远迅速站到我前面,
从腰间掏出什么东西——一把折叠军刀,刀刃在晨光中闪着寒光。"退后!
"他用缅甸语厉声喝道,"这孩子还有救!"村民们停下脚步,但火把仍在燃烧,
愤怒的喊叫声此起彼伏。我抱着昏迷的孩子,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。
陆远的背影像一堵墙挡在我们前面,但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对抗整个村子的恐慌?就在这时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