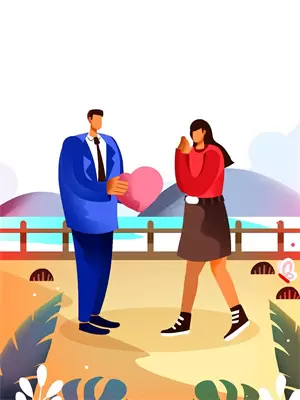第一幕,105年3月,浴室对话田玉英涂口红的动作突然僵住。镜子里浮动的白雾间,
女儿赤裸的肩颈上蜿蜒着青紫色的淤痕,像一条毒蛇盘踞在雪地里。
浴室顶灯在潮湿空气里晕开白色光晕,把少女单薄的身影拓印在磨砂玻璃上。“妈,
你闻到了吗?”苏晚晴的声音混着水雾飘来,像从腌渍多年玻璃罐里捞出,
“阁楼里都是他的酒气。”花洒喷出的水珠突然变得滚烫,田玉英慌忙关掉龙头。
蒸汽顺着瓷砖往下爬,在少女锁骨处的淤青上凝结成水珠。那些淤痕的形状很特别,
像是有人用拇指和中指掐住天鹅的脖颈,留下的半月形印记。
“你爸他……”田玉英忽地手抖,睫毛膏晕开了,在眼睑外拖出一道长长的黑痕,
“他压力大,你要体谅……”镜子突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
苏晚晴的指甲在镜面上划出五道扭曲的裂痕,水珠顺着裂缝流下来,像镜子在流泪。
“上个月是左腿,这个月是脖子。”少女的指尖按在淤青上,
皮肤下的毛细血管绽开细小的血点,“下次该用什么还债?‘玻璃珠子’?还是‘花园’?
”窗外传来闷雷的轰鸣,浴室顶灯忽明忽暗。田玉英看见女儿瞳孔里浮动着奇异的光,
像是暴雨前聚集的铅灰色云层。她突然想起十六年前产房里那盏手术灯,
也是这样刺眼的白光里,助产士说新生儿的眼睛清澈得像玻璃珠子。
“小晚……”她伸手想触碰女儿肩头的淤青,却在即将碰触的瞬间蜷起手指。
梳妆台上的某品牌五号香水混着血腥气钻进鼻腔,那是上周苏大贵扔给她的“封口费”。
少女忽然笑起来,笑声割裂空气,瓷砖裂痕间渗出霜痕:“昨晚他锁着我的时候,
你就在楼下看电视对不对?片尾曲响了三遍。”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她苍白的脸上,
“紫薇说‘山无棱天地合’的时候,我的指甲在阁楼地板上抓出了血。
”田玉英的口红掉进洗手池,在瓷壁上拖出猩红的轨迹。
她终于看清女儿锁骨处的淤青根本不是指痕——而是牙齿咬出的半月形伤口,
边缘结着暗红的血痂。田玉英捡起弯腰捡起口红时,余光瞥见苏婉晴缩在浴缸角落,
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陶瓷娃娃的手臂——那是她5岁生日时田玉英送的礼物。
田玉英缓缓阖上双眸,在心底给出了答案:如果我护着你,明天被拖进赌场的就是我。
”她盯着女儿锁骨上的齿痕,想起几个月前阿鹏在巷口冷笑。“苏太太,
你丈夫押的可是氵舌人利息。”田玉英离开浴室,一道蝶影在身后闪过。“妈妈,
阁楼的蝴蝶在啃我的眼睛。”她指尖按向淤青,皮肤下鳞粉闪烁,
“它们说要带我去看爸爸的……”水珠滚过少女的脖颈,青紫淤痕如活物般蠕动,
蓝闪蝶鳞粉从皮下渗出,将伤口修补成苍白的月牙。第二幕,苏大贵之死阁楼,
怀表秒针在空中顺时针转动,传来金属摩擦声,一只蓝闪蝶翩然而至,
附在轻微碎裂的玻璃表盖上。地面,人影扭曲的瘫倒着,身下血泊渐次铺开。
暴雨倾盆而下时,急诊室的消毒水味裹着血腥气扑面而来。田玉英看着白布下扭曲的人影,
护士说坠楼的男人口袋里还装着赌场借据。她转身时撞见苏晚晴在笑,
少女空洞的眼眶里淌出两行血泪,像极了被暴雨打落的凤凰花瓣。停尸间冷气嘶嘶作响,
一只蓝闪蝶突然从苏晚晴发间振翅飞出,撞碎在监控摄像头的玻璃罩上。田玉英这才想起,
前天收债人上门时,女儿曾轻声说:“你看,蝴蝶撞向火焰的样子,多像我们啊。
”田玉英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法医的橡胶手套与不锈钢托盘碰撞声在停尸间回荡。
她盯着苏大贵扭曲的右手指节——那里还沾着半片蓝闪蝶的磷粉,在冷光下泛着诡异的幽蓝。
田玉英的脸色如纸般苍白,眼神中透着慌乱与不安,她强装镇定地操持着苏大贵的后事。
殡仪馆内,冷气裹着消毒水味,刺痛田玉英的鼻腔,她机械地签署着各种文件,
目光空洞地看着工作人员将苏大贵的尸体抬进灵堂。灵堂里弥漫着沉重的气息,
那一束束白色的花,无声诉说着哀伤。周围人的窃窃私语像针一样刺痛着她的耳朵,
可她只能装作听不见,脸上挂着虚伪的悲伤。第三幕,蛛网一当晚路人报警,
警方的调查人员很快到来,他们严肃的表情和锐利的眼神让田玉英感到窒息。“田女士,
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苏大贵先生坠楼的具体情况,希望你能配合我们。”一位年轻的警察说道。
田玉英勉强扯出一抹僵硬的笑容,“我会全力配合,只是我也很震惊,
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来。”她的右手下意识抚上胸口,心脏剧烈地跳动,
仿佛随时会破胸而出。“当时我在浴室洗澡,没听到什么动静,
等我出来就发现他已经……”说到这里,她突然停住,装作悲痛欲绝地低下头,
用手在脸颊上抹了抹并不存在的泪水。压抑的氛围中,一只蓝闪蝶如同不速之客,
从窗外飞了进来,在屋内翩翩起舞。它那闪烁着幽蓝光华的翅膀,格外刺眼。
田玉英面露惊恐,她下意识地伸出手,慌乱而急切地驱赶着那只蝴蝶。
警察的制服在钨丝灯下泛着冷灰,而蓝闪蝶的翅膀晕出诡异的萤光,田玉英知道,
只有自己看得见那抹幽蓝。“这只蝴蝶怎么会飞进来?”警察皱了皱眉头,疑惑地问道。
田玉英强装镇定:“可能在找食物,这个季节蝴蝶本来就多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发颤,
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,指关节都泛着青白。警察对田玉英产生一丝怀疑。
那只蓝闪蝶似乎故意挑衅她,在她头顶盘旋了几圈后,轻盈地落在了苏大贵的遗像上。
田玉英急忙别过头去,不敢直视那只蝴蝶,仿佛它身上带着某种致命的诅咒。
警方开始对监控进行细致的排查。每一个画面、每一秒的定格,都像是一把钥匙,
试图打开真相的大门。他们终于寻觅到那段关键视频。然而,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,
仅仅过了几秒,画面静止。“田女士,监控记录显示,苏先生坠楼前最后接触的人是您女儿。
”警察的声音像生锈的手术刀划过铁板,“但存储卡被人为破坏了。”警方意识到,
有人在背后操纵,这起坠楼案不简单呐。在警方询问的过程中,田玉英努力编造谎言,
试图掩盖真相。然而,每当她抬起头,总能看到角落里有一只蓝色的蝴蝶在轻轻颤动翅膀,
那幽蓝色的光芒让她的心跳陡然加快。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,可那蝴蝶却越来越清晰,
仿佛在嘲笑她的自欺欺人。田玉英目送警察离开,忽然,手机震了一下,
垃圾短信中混着一串乱码:“**交易中止,**务必销毁。
夜里的争吵——“你真以为赌场会放过?连自家人的乌珠都敢挖!”窗外的蓝闪蝶扑向路灯,
翅膀在玻璃上投出阴影。第四幕,赌场一恍惚间,田玉英正走在一条昏暗的街道上,
两旁的路灯散发着微弱而昏黄的光,将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。
一辆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的停在她面前,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车门被粗暴地推开。
几个凶神恶煞的收债人从车上下来。他们身形魁梧,脸上带着一股子狠厉。
为首的男人是阿鹏,脖颈处有一个蓝闪蝶纹身,精致的纹路与色彩,
竟和苏晚晴房间里的画相差无几。纹身翅脉由数字和“玻璃珠”简图交织而成,
蝶腹处刻着“玻璃珠:A+”。他们迅速呈扇形散开,将田玉英的退路严严实实地堵住,
密不透风。阿鹏恶狠狠地盯着她,目光中隐隐有凶光闪过:“田玉英,
苏大贵欠我们的钱可不能就这么一笔勾销,识相的就赶紧还钱!”话音刚落,
一张单子被猛地甩在田玉英的脸上,纸张与皮肤接触的瞬间,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
她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,待视线聚焦在那单子上触目惊心的数额时,整个人如遭雷击。
田玉英瞪大眼睛,惊恐地往后退了几步,声音颤抖得几乎不成调:“我……我没有钱,
我不知道他欠了你们这么多钱。他已经死了,你们找我也没有用。”“他死了,
作为他的家人,这笔债你得还。”阿鹏冷笑了一声,嘲讽:“别装糊涂了,
今天你要是不还钱,就跟我们去赌场走一趟。”说罢,他们快速上前,
饿狼扑食般抓住田玉英的胳膊,用力将她往车上拖去。田玉英拼命地挣扎,
人却离车门越来越近。大声呼喊:“救命啊!救命啊!”凄惨的声音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绝,
周围没有人回应她的呼喊。车里,
田玉英透过车窗看到了诡异的一幕:苏晚晴在不同的时空里,重复上演遭人蹂躏的惨状。
每一次伤害,她的眼神都凝聚着足以令人胆寒的绝望和怨恨。看得田玉英心里发慌。
田玉英的眼泪夺眶而出,她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。倘若当初,
她没有默许苏大贵的恶行,如果她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而狠心伤害苏晚晴,
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。她知道,这一切都是苏晚晴的复仇。到达赌场后,
田玉英被押到一个宽敞的房间。阿鹏坐着把玩一块青铜怀表,表盖缝隙闪过蓝光,
像蝶翅擦过金属。赌场穹顶的彩色玻璃窗在月光下散发着诡异的光芒,定睛细看,
瞬间头皮发麻,哪里是什么玻璃窗,分明是巨型蝶蛹!
隐隐约约浮现出借贷者被蚕食的可怖影像。田玉英吓得赶紧别过头去,阿鹏见状,
怎会轻易放过她,满脸满脸戾气地走到田玉英面前。只见他猛地伸出粗壮的手,
一把揪住田玉英的头发,硬生生将她的头掰转回来,逼迫她不得不直面那令人胆寒的蝶蛹。
“田玉英,瞧瞧这一切,都是你丈夫犯下的罪孽。”阿鹏冷冷地说道。田玉英只觉眼前一黑,
绝望地瘫倒在地,阿鹏的蝴蝶刀擦过田玉英的眼角。赌场里,昏黄的灯光摇曳不定,
烟雾弥漫。田玉英如一只无助的羔羊。阿鹏下令,手下人架起田玉英,
粗暴地将她拖拽进下一个房间,房间里整齐的摆满了各种玻璃罐,
罐子里漂浮着借贷者的“玻璃珠子”,闪烁着幽冷的光。
田玉英下意识地避开那些“玻璃珠子”,不敢与之对视。满心慌乱之时,
一个声音从角落的冷藏柜传来:“田玉英,你终于来了。”她的身体猛地一颤,
缓缓地转过头,看到苏大贵的尸体躺在冷藏柜里,
他的脖颈处飞出了一只带着记忆磷粉的蓝闪蝶。“苏大贵,你……你怎么还会说话?
”田玉英惊恐地问道。苏大贵冷笑了一声,一字一顿道:“田玉英,
你真以为自己能从这滩浑水里全身而退?掩盖真相,警察会查不出来吗?”刹那间,
田玉英的脸色煞白,身体忍不住颤抖,带着哭腔说:“我知道错了,我会想办法弥补的。
”苏大贵厉声说道:“你弥补不了,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苏晚晴不会轻易饶过你,
她会让你付出代价。”田玉英猛地抬起头,满脸恨意的啐了一口,大声吼道:“呸,苏大贵,
你才是真正染血的凶手,她没放过你,同样也不会放过我!”田玉英绝望地闭上了双眼,
泪水顺着脸颊潺潺滑落。她心里清楚,自己已然深陷一个无法逃脱的困境。第五幕,
超自然干扰某天傍晚,田玉英回到家中,客厅的灯光闪烁不定,
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窥视着她。倏忽,一阵怪异的声响从阁楼上传来,
像是有人在低声啜泣。她的心跳陡然加快,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。但她还是鼓起勇气,
脚步迟缓地朝着阁楼走去。阴暗逼仄的阁楼似乎还残留着苏晚晴被侵害时所留下的痛苦气息。
潮湿的墙壁上,水珠缓缓滑落,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,宛如苏晚晴那无声的悲泣。
田玉英小心翼翼地在阁楼里查看了一番,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随后,她走进自己的房间,
打算静下心来整理一下思绪。可就在这时,她不经意间瞥向梳妆台,
镜子里竟浮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象。镜子中,苏晚晴那苍白的脸逐渐浮现,
眼神冷冷地注视着她。田玉英惊恐地后退,却听到一阵窸窸窣窣,一群蓝闪蝶从镜子中飞出,
围绕着她飞舞。它们的翅膀闪烁着诡异的蓝光,每一次颤动都像是在提醒她曾经犯下的罪孽。
田玉英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,额头上冒出了冷汗,“别过来!别过来!”她声嘶力竭地喊道,
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。那些蓝闪蝶并没有理会她的呼喊,反而越聚越多,
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田玉英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着,
身体不由自主地向漩涡中心飘去。窒息感袭来,
田玉英看到了一些恐怖的画面:苏晚晴在阁楼里被蹂躏,
自己在浴室里默许伤害的画面;苏晚晴幼时灵动如星辰般的眼睛……苏晚晴死前绝望的眼神。
她的眼泪夺眶而出,心中充满了悔恨和自责。田玉英在蝶群的包裹中,
恍若回到了十九年前的医院,那刺眼的手术灯光下,一只蓝闪蝶静静地停驻在灯上,
就像现在一样,冷冷地看着她。在她的眼前,清晰地浮现初次诞下新生命的那一幕。
手术灯明亮的光晕中,一只蓝闪蝶悄然停歇,它的翅膀闪烁着诡异的光芒。
她望见彼时青春正好的自己,无助地躺在手术台上,眼神空洞得如同干涸的古井,
医生手持冰冷的手术器具,语气冷淡不带一丝人间烟火,问道:“准备好了吗?
”她机械地点了点头,泪水顺着脸颊簌簌滑落。就在此刻,一只蓝闪蝶飞到了她的眼前,
它唰的一下变成一颗“玻璃珠子”,那里边似乎蕴含着无尽的怨恨。
田玉英拼尽全力想要逃离,却无法动弹。“妈妈,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
”一道轻柔却满含哀怨的声音,幽幽响起,那是苏晚晴的姐姐——出生前就注定消亡的孩子。
田玉英痛苦地紧闭双眸,悔恨喊道:“对不起,对不起!”她的身体在蝶群中瑟瑟发抖,
似狂风肆虐下的一叶孤舟。记忆再次闪回,殡仪馆的钨丝灯管在晨雾中嗡嗡作响,
田玉英攥着储存卡的右手突然刺痛——那些蓝闪蝶的磷粉正在渗入皮肤,
沿着血管织成发光的经络。当她将存储卡按进碎纸机时,齿刃间突然迸出十六年前的月光。
89年秋蝉鸣泣的深夜,二十五岁的田大贵自认镇定地坐在产科外面的走廊。
赌场马仔的鳄鱼皮鞋踩着《献给爱丽丝》的旋律逼近,产房门缝漏出的白光里,
新生儿啼哭混着护士惊呼:“眼珠颜色怎么在变?”此刻碎纸机喷出的不是纸屑,
而是泛黄的诊断书碎片。田玉英惊恐地发现每片纸屑都在重新拼合,
蓝闪蝶的鳞粉像金缮修复的釉彩,将“视神经先天缺陷”修补成“角膜人为损伤”。
田玉英默许苏大贵在新生儿筛查报告上偷偷伪造视力检测结果。她的双手颤抖着,
愧疚如同藤蔓般在她心中疯狂生长。“我当时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啊,
我不想失去所拥有的一切。”她神情落寞,嘴唇嗫嚅着。声音中满是无奈和悲哀。“妈,
你以为你能逃脱吗?”苏晚晴的质问在她耳边响起,四面八方都有。田玉英紧紧捂住耳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