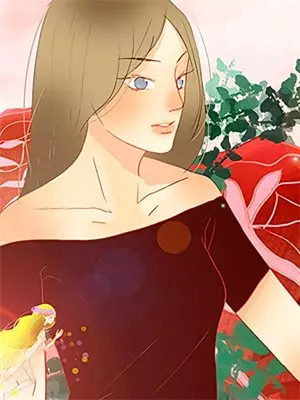
全家穿越到饥荒古代。我利用现代知识,拼命挖野菜、设陷阱养活全家。
老公和儿女却嫌弃野菜苦,嫌弃兔肉腥。逃荒路上,他们为了换两块白面饼,
把我卖进了青楼。妈,你徐娘半老还有点姿色,为了我们全家,你牺牲一下吧。
我在受尽屈辱中咬舌自尽。再睁眼,回到了刚穿越那一刻。看着手里仅剩的半个红薯,
老公和儿女正眼巴巴地等着分配。我二话不说,三口两口把红薯塞进嘴里咽了下去。
面对他们震惊的眼神,我打了个饱嗝。看什么看?既然都要饿死,
做个饱死鬼总比养一群白眼狼强。1.陈建业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,那一瞬间,
他脸上的皮肉都在抽搐,像是见了鬼。林梅!你疯了?那是最后一点吃的!
小宝和小雪都还饿着,你怎么敢自己全吃了?他扬起手就要往我脸上招呼。上一世,
我就是为了这半个红薯,省下来给他们分了,自己饿得喝了三天凉水,最后落下一身胃病,
还要被他们嫌弃身子骨弱,拖累行程。我身子一侧,抬腿就是一脚踹在他膝盖窝里。
常年练瑜伽和这几年做家政练出来的力气不是盖的。陈建业哎哟一声,
跪在地上吃了一嘴的黄土。妈!你干嘛打爸?女儿陈雪尖叫起来,
那声音尖锐得像是指甲划过黑板,刺得人耳膜生疼。儿子陈宝也从那块破草席上跳起来,
指着我的鼻子骂:你个老不死的,有吃的自己独吞,你想饿死我们啊?自私自利的老虔婆!
听听。这就是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好儿女。上一世,我为了给陈宝抓一只野鸡补身子,
差点跌下悬崖摔死。结果他嫌野鸡肉柴,塞牙,转头就倒给了路边的野狗。陈雪更是娇气,
我说野菜苦,让她忍忍,她哭着喊着要喝奶茶,还要把我不容易攒下的救命水拿去洗脚,
说脚上沾了泥不舒服。我那时候怎么就瞎了眼,觉得他们只是不适应环境呢?
这哪里是不适应,这就是坏,是骨子里的烂。我冷笑一声,
拍了拍手上的红薯渣:我是自私,既然我自私,那从现在开始,咱们各走各的阳关道。
这荒郊野岭的,谁也别指望谁。我说完,转身就要去收拾那堆破破烂烂的行李。
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。我们是整栋别墅穿越过来的,但房子落地就塌了,
能用的东西少之又少。我眼疾手快,从废墟边上捡起那把幸存的水果刀,
又摸走了唯一的打火机,揣进贴身口袋里。林梅,你把打火机放下!陈建业爬起来,
眼红得像兔子,那是我的!你的?我把玩着刀刃,寒光在正午的日头下格外刺眼,
写你名字了?还是你叫它一声它能答应?陈建业怂了。他就是个窝里横,
平时在公司连个屁都不敢放,回家只会对我颐指气使。看到刀,他咽了口唾沫,
换了副嘴脸:老婆,别闹了。咱们一家人在这种鬼地方,得团结。刚才是我不对,
我不该凶你。但你是当妈的,怎么能跟孩子抢食吃呢?就是,妈,你太不懂事了。
陈雪在一旁帮腔,捂着肚子一脸委屈,我都快饿晕了,你还有心思闹脾气。
我理都没理他们,背起那个装着两件厚衣服的包裹,找了根结实的木棍当手杖。团结?
那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。你们,配吗?我头也不回地往树林深处走去。
根据上一世的记忆,这片林子虽然干旱,但深处还有些能吃的树根和草药,
甚至运气好能碰到还没干涸的水洼。但我绝不会再告诉他们了。
身后传来陈宝气急败坏的吼声:让她走!我看她能活几天!等她饿得受不了了,
还得跪着回来求我们!爸,我饿……陈雪带了哭腔。别急,爸带你们找吃的,
不就是野外求生吗?电视上都演过,简单得很!
陈建业自信满满的声音随着风飘进我耳朵里。简单?呵,真是厕所里点灯——找死。
2.这一带是典型的北方旱地,连着三年大旱,地皮裂得像乌龟壳,树皮都被流民扒光了。
我凭着上辈子的经验,在一处背阴的山坳里找到了一丛还没枯死的刺儿菜。
这种野菜虽然口感粗糙,但能填饱肚子,也没毒。我挖了一大捧,
又在石头缝里抓了几只肥硕的土休。上一世,我抓这东西回去,被陈雪嫌弃得要死,说恶心,
死活不吃,最后还是陈建业为了在这个新世界立威,逼着我把肉烤了,
他却把自己那份给了儿子,自己假惺惺地啃骨头,还要骂我没本事抓不到兔子。现在,
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找了个避风的土坑,我熟练地生火,剥皮,穿串。没有调料,
但肉香很快弥漫开来。就在我刚把一只烤得焦黄的土休塞进嘴里时,草丛那边传来了动静。
好香啊!我就说这边有味道!陈宝那公鸭嗓子一响,
紧接着三个人影就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。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,
陈雪的高跟鞋早就跑丢了一只,现在光着一只脚,踩在满是荆棘的地上,
那狼狈样活像个逃难的叫花子。看到我手里的烤肉,陈宝的眼睛瞬间绿了,
像饿狼一样扑过来。妈!你果然藏了好东西!快给我!他伸手就抢,
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,仿佛这东西天生就该是他的。我坐着没动,手腕一翻,
那把水果刀笃的一声插在他脚尖前的泥地里。刀柄还在嗡嗡作颤。陈宝吓得猛地缩回手,
一屁股坐在地上,脸色惨白。再伸爪子,我就给你剁了当加餐。
我慢条斯理地嚼着嘴里的肉,眼神冷得像冰。陈建业气喘吁吁地赶上来,看到这一幕,
又惊又怒:林梅!你是要杀人啊?那是你亲儿子!亲儿子又怎样?想要吃的,
自己去抓。我指了指不远处的石缝,那里多得是,只要你们不嫌恶心。
陈雪看着我嘴边流下的油渍,馋得直咽口水,哪里还顾得上嫌弃:妈,我不嫌弃,
你分我一点吧,我真的走不动了……想吃?我挑眉。想!三个人异口同声。
拿东西换。陈建业愣住了:换?我们哪有东西?钱都在手机里,这鬼地方又没信号!
我目光落在陈建业手腕上那块名表上,那是他去年升职为了充门面买的,花了十几万。
表给我。陈建业下意识捂住手腕:这可是劳力士!你就拿几只破蜥蜴换我的劳力士?
你疯了吧!在现代它是劳力士,在这里,它就是块废铁。但在我这儿,
它能换你们一顿饱饭。我撕下一条肉,故意在他们面前晃了晃。肉香这种东西,
在极度饥饿的人面前,比什么毒品都上头。陈宝和陈雪已经开始推搡陈建业了。爸!
你给她吧!一块破表算什么,回去再买就是了!就是啊爸,你想饿死我们吗?
陈建业被逼得没办法,咬着牙把表摘下来,狠狠地扔给我:给你!你个吸血鬼!
连家里人的便宜都占!我接住表,随手揣进兜里,指了指旁边剩下的两只生蜥蜴:成交。
自己烤去。生的?!陈雪尖叫,我们要吃你手里那个烤好的!那得加价。
我淡淡道,你要是把你脖子上那条金项链给我,我也不是不能考虑。
陈雪下意识捂住脖子,那是她刚谈的富二代男朋友送的。最后,他们还是没舍得再出钱,
骂骂咧咧地拿着两只生蜥蜴去旁边生火。可惜,他们连打火机都没有。
陈建业试着用石头砸火星,砸了半天,手都砸破了皮,连根毛都没点着。
看着他们三个对着生肉大眼瞪小眼,最后饿得受不了,陈宝居然想生吃,
结果刚咬一口就被腥得吐了一地黄水。我心里那叫一个痛快。这就是报应。3.夜里,
气温骤降。这一带虽然干旱,但晚上冷得像冰窖。我找了个背风的树洞,铺上厚厚的干草,
裹着两件羽绒服缩在里面,虽然不算暖和,但至少能睡着。陈家那三口子就惨了。
他们没厚衣服,我穿越前正在收拾换季衣物,把他们的厚衣服都收进柜子深处了,
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为了摆拍穿的薄衬衫和小裙子。半夜,我听到外面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。
妈……妈你醒醒……让我们进去挤挤吧……陈雪冻得牙齿打颤的声音在树洞外响起。
林梅,我是你男人!你要是敢让我们冻死在外面,你就是谋杀!
陈建业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,却还带着那股子令人作呕的命令口吻。我翻了个身,
把耳朵堵上。上一世,逃荒路上也遇到过寒潮。
那时候我把仅有的一床被子盖在他们三个身上,自己缩在边上挡风,冻得高烧三天,
还要被骂身子热得像火炉,烫着他们了。这一世,该轮到他们享受这种天伦之乐了。
见我不理,陈宝居然想硬闯。他刚把头探进来,我就一脚踹在他脸上。滚。简单一个字,
却带着浓浓的杀气。陈宝哀嚎一声滚了出去,紧接着外面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咒骂声。
骂我毒妇,骂我不得好死。骂吧,骂得越凶,说明他们越有精神,离死还早着呢。后半夜,
外面安静了。我也没敢睡死,毕竟这荒郊野岭的不只有狼,还有比狼更可怕的人心。
第二天一早,我是被一阵嘈杂的人声吵醒的。探头一看,只见不远处的土路上,
稀稀拉拉地走过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民。这是逃荒的大部队到了。
陈家那三口子正像看到了救星一样,扑上去拉住一个路人就问:大哥,这是哪儿啊?
有没有警察局?我们要报警!那路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们,一把推开陈建业:滚开!
什么警察局?疯子!陈建业不死心,又拉住一个看起来稍微体面点的老头:大爷,
借个手机用用行吗?我给你转账,一万块!不,十万!那老头也是个逃荒的,
不过是个老江湖,听到钱字,眼睛眯了眯。手机没有,不过老汉我也饿了两天了,
你们要是有吃的,我也能给你们指条明路。陈建业一听有戏,
连忙指着我这边:我有老婆!我老婆那儿有吃的!还有打火机和刀!我心里咯噔
一下。这狗东西,转眼就把我卖了。那老头顺着他的手指看过来,
目光在我身后的包裹和腰间鼓囊囊的地方扫了一圈,眼神变得贪婪起来。不仅是他,
周围几个原本麻木赶路的流民,听到吃的和刀,也都停下了脚步,
眼神不善地围了过来。在荒年,一把刀,一个打火机,那就是命。陈建业见状,
得意地朝我喊:林梅!快把东西拿出来分给大家!这种时候要互帮互助!
大家都是落难的人,你不能这么自私!陈雪也跟着起哄:就是!妈,你别太吝啬了,
大家都会感激你的!这是想利用群众压力逼我就范?还是熟悉的道德绑架。
如果是上一世的我,可能真的会为了息事宁人,或者是为了那个所谓的面子,
把东西拿出来。但现在的我,只会觉得好笑。我站起身,拍了拍身上的土,一手握着刀,
一手拿着那个打火机,啪的一声点燃火苗,又熄灭。东西就在这儿。
我环视了一圈围上来的流民,大概有七八个青壮年,眼神都带着凶光。谁想要,拿命来换。
我的声音不大,但足够清晰。陈建业急了:大家别听她的!她就一个女人,吓唬谁呢!
抢了她的东西,咱们平分!这一嗓子,彻底点燃了那几个流民的贪欲。
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狞笑着走出来:大妹子,听你男人的话,把东西交出来,
哥哥保证不伤你。陈建业躲在后面,脸上露出了阴毒的笑。他是想借刀杀人,
既能拿到东西,又能教训我,甚至……如果我被这些人弄死了,他也正好甩掉我这个累赘
。好一招借刀杀人。就在大汉要扑上来的瞬间,我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,高高举起。
我看谁敢动!4.我手里举着的,是一个小小的玻璃瓶。里面装着半瓶透明的液体。
这是我穿越前随手塞进包里的防狼喷雾,超强力浓缩辣椒水,那劲道,
能让一头成年公牛跪下叫妈。但在这些古人眼里,这晶莹剔透的瓶子,
精致得像是天宫里的宝物。大汉愣住了,脚步一顿:这是啥?剧毒。我冷冷地扯谎,
见血封喉的毒药,只要我把瓶子摔碎,这里的气味散开,方圆十丈之内,人畜不留。
为了增加可信度,我用刀柄轻轻敲了敲瓶身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流民们虽然凶悍,
但更是愚昧惜命。听到毒药两个字,又看着那从未见过的精致玻璃器皿,
一个个都不敢动了。陈建业急了:别听她瞎扯!那就是个破化妆水瓶子!哪有什么毒药!
是吗?我看向陈建业,嘴角勾起一抹讥讽,那你过来试试?只要你敢走近三步,
我就让你尝尝这『化尸水』的味道。陈建业被我看得心里发毛。他其实也不确定那是什么,
毕竟家里的瓶瓶罐罐太多,他从来没关心过。万一真是这疯婆娘搞出来的什么怪东西呢?
他缩了缩脖子,不敢上前。那个领头的大汉见陈建业都怂了,心里也没底,
骂了一句:晦气!碰上个疯婆子!他狠狠瞪了陈建业一眼:你不是说她好欺负吗?
差点害死老子!说完,大汉一挥手,带着人散开了。危机暂时解除。我收起喷雾,
冷冷地看着陈建业一家三口。他们现在的脸色比吞了苍蝇还难看。林梅,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