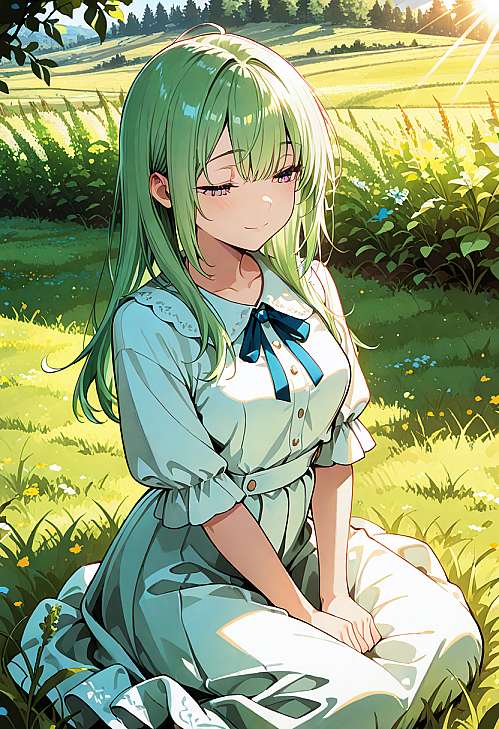柳知远手里捏着那把描金的折扇,扇骨是沉香木的,扇面是请江南名家画的《仕女图》。
他觉得这才是生活。比起那个只会舞刀弄枪、一身汗臭味的粗鲁婆娘,眼前这位林表妹,
才叫真正的女人。“表哥,这三千两银子买一块砚台,若是姐姐回来了……”林黛柔蹙着眉,
手里的帕子绞得死紧,眼里却闪着贪婪的光。“提她作甚?”柳知远冷哼一声,
把那方端砚往怀里一揣,像是揣着自个儿的命根子,“这府里姓柳!
她霍无双不过是个只会杀猪宰羊的武夫,懂什么风雅?再说了,她死在边关才好,
省得回来碍我的眼。”他转过身,对着满屋子的清客相公们拱了拱手,
脸上挂着那副自以为怀才不遇、实则小人得志的笑。“诸位,今日这‘流觞曲水’的酒钱,
全算在本官账上!咱们读书人,讲究的就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!”底下一片叫好声。
柳知远飘了。他觉得自己此刻就是这京城里的文曲星下凡。直到一声巨响。
那扇花了他五百两银子、用黄花梨木雕刻的“听雨轩”大门,被人一脚踹飞了进来。
木屑横飞,直接砸进了他面前那碗刚温好的女儿红里。1霍无双站在自家大门口的时候,
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地界儿。原本挂着御赐“镇国将军府”金字牌匾的地方,
现在挂着一块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破木头,
上书三个歪歪扭扭的大字——“听雨轩”门口那两尊威风凛凛的石狮子,
脖子上竟然被挂了大红花,嘴里还塞着绣球,活像两个刚被逼良为娼的壮汉。
霍无双眯了眯眼。她手里的马鞭在掌心轻轻敲了两下。“这就是本将军的府邸?
”旁边的副将王铁柱吓得脸上的横肉都在抖,咽了口唾沫:“大将军,
按地图标示……经纬度……啊不,按方位来看,确系此处无疑。只是这风格……略显骚气。
”霍无双冷笑一声。好一个柳知远。当初这厮穷得连赶考的盘缠都没有,
是霍家老爷子看他写得一手好字,人又长得人模狗样,这才招了赘婿。霍无双出征三年,
在边关吃沙子、喝马尿,跟蛮子拼刺刀。这厮倒好,在后方搞起了“文艺复兴”“进去。
”霍无双把缰绳往王铁柱手里一扔,大步流星地往里走。她这一身黑铁甲胄还没卸,
走起路来咔咔作响,像是带着一股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煞气。刚进二门,
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咿咿呀呀的丝竹之声,夹杂着男人放浪的笑声和女人的娇嗔。
原本用来演武的校场,此刻被挖了个大坑,里面灌满了水,上面飘着几个酒杯。
一群穿着宽袍大袖、瘦得跟白斩鸡似的书生,正坐在水边,摇头晃脑地吟诗作对。“好诗!
好诗啊!”“柳兄这句‘红袖添香夜读书’,简直是神来之笔!”“哪里哪里,
不过是偶感风月,不值一提,不值一提啊!”被簇拥在中间的那个男人,
穿着一身骚包的粉色长衫,手里摇着折扇,脸上涂着厚厚的粉,笑得跟朵烂桃花似的。
正是霍无双那个“才高八斗”的夫君,柳知远。霍无双停下脚步,深吸了一口气。这味道。
不是脂粉味,是钱烧焦的味道。这哪里是家,这分明是敌军攻占了我方指挥部,
正在举行庆功宴!她没说话,只是解下了腰间的佩刀,“哐当”一声,
重重地拍在了那张摆满了珍馐美味的紫檀木桌子上。这一声响,比惊雷还炸耳。
那群正在“流觞曲水”的文人雅士,吓得手里的酒杯掉了一地。柳知远正闭着眼享受马屁呢,
被这一声吓得浑身一哆嗦,手里的折扇直接掉进了水沟里。“哪个不长眼的狗奴才!
敢惊扰本官的雅兴!”柳知远怒骂着睁开眼。然后,
他就看见了一张黑得像锅底、冷得像冰窖的脸。
还有那把还在微微震颤的、沾着暗红色血迹的横刀。2柳知远愣了足足有三息的功夫。
他的脑子里此刻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“天人交战”这婆娘不是说战事吃紧,
还得个一年半载才能回来吗?怎么今儿个就跟个活阎王似的杵在这儿了?
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。他是谁?他是读书人!是圣人门徒!
怎么能怕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妇道人家?柳知远清了清嗓子,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威严架势,
虽然他的腿肚子还在打转。“无双?你……你回来怎么也不提前通报一声?这般冒冒失失的,
成何体统!”他指着桌上的刀,一脸嫌弃地用袖子掩住口鼻,“还有,这一身的血腥气!
简直有辱斯文!还不快去后堂沐浴更衣,别冲撞了我的贵客!”霍无双气笑了。她这一笑,
露出一口森森白牙,看得旁边的王铁柱都忍不住往后缩了缩。“通报?”霍无双伸手,
两根手指捏起柳知远面前那个精致的白玉酒杯。“啪!”酒杯在她指尖炸成了粉末。
白色的粉末簌簌落下,洒进了柳知远的酒碗里。“本将军回自己的府邸,
还需要向你这个吃软饭的通报?”全场死寂。那些个清客相公们一个个缩着脖子,
恨不得把脑袋塞进裤裆里。柳知远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“吃软饭”这三个字,
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逆鳞。“你……你粗鄙!不可理喻!”柳知远气得浑身发抖,
指着霍无双的手指头都在哆嗦,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!古人诚不欺我!我乃朝廷命官,
你……你竟敢如此羞辱于我!”“朝廷命官?”霍无双往前逼近了一步。
她比柳知远高出半个头,此刻居高临下地看着他,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不知死活的蚂蚱。
“柳知远,你那个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,还是老娘拿军功给你换来的。你是不是忘了?
”“你!”柳知远气结。就在这时,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柳知远身后传了出来。“姐姐,
你莫要怪表哥。表哥也是为了结交名士,为日后的仕途铺路呀。
”一个穿着一身素白孝服似的女人,弱柳扶风地走了出来。她长得倒是颇有几分姿色,
眉眼含愁,一副随时都要断气的模样。正是柳知远的远房表妹,林黛柔。她手里端着一杯茶,
走到霍无双面前,怯生生地说:“姐姐一路辛苦,先喝口茶消消气吧。表哥他是读书人,
面皮薄,姐姐这般说话,确实有些伤人了。”霍无双低头看了看那杯茶。茶汤碧绿,
上面还飘着两片嫩叶。好一杯顶级绿茶。霍无双没接。她只是淡淡地扫了林黛柔一眼,
那眼神锐利如刀,仿佛能直接把林黛柔那点小心思给剖开晾在太阳底下。“你是哪个营的?
”霍无双突然问。林黛柔一愣:“什……什么?”“本将军问你,你是哪个营的军妓?
还是负责烧火的丫头?见到主将,为何不跪?”这一句话,直接把林黛柔给问懵了。
她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,那叫一个快,跟开了闸似的。
“表哥……你看姐姐她……”林黛柔身子一软,顺势就要往柳知远怀里倒。
柳知远顿时心疼坏了,连忙伸手去扶,一边扶还一边瞪着霍无双:“霍无双!你太过分了!
柔儿是我的表妹!也是这府里的贵客!你怎么能把她和那些……那些下贱人相提并论!
”“贵客?”霍无双冷哼一声。“既然不是军中之人,那就是擅闯军事重地。”她突然抬腿。
这一脚,快如闪电,重若千钧。“砰!”柳知远连人带那把描金折扇,直接被踹飞了出去,
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,最后“噗通”一声,精准地落进了那个挖好的水坑里。
水花四溅。满座皆惊。霍无双收回腿,拍了拍靴子上的灰,
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“本将军的规矩,闲杂人等,不得在校场逗留。违者,
斩。”3水坑不深,也就刚没过腰。但对于柳知远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来说,
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。他在水里扑腾着,像只落汤鸡,嘴里还吐着脏水:“救命!杀人啦!
谋杀亲夫啦!”那些个清客相公们这才反应过来,七手八脚地去捞人。
林黛柔更是吓得花容失色,尖叫着:“表哥!表哥你没事吧!”霍无双连看都没看一眼,
转身走到主位上,大马金刀地坐下。“王铁柱。”“末将在!”“清场。
”霍无双吐出两个字。王铁柱咧嘴一笑,露出一口大黄牙,
从腰间抽出那把跟门板一样宽的大刀,往地上一杵。“各位相公,是自己滚,
还是让俺送你们一程?”那群文人哪见过这阵仗?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,连鞋都顾不上穿,
抱着头鼠窜而去。眨眼间,原本热闹非凡的“听雨轩”,就只剩下了还在水里扑腾的柳知远,
和瘫坐在地上的林黛柔。柳知远终于被捞了上来。他浑身湿透,头发散乱,
那身粉色的长衫贴在身上,活像个刚从染缸里爬出来的鬼。“霍无双!我要休了你!
我要休了你!”柳知远一边哆嗦,一边指着霍无双咆哮,“你这个泼妇!悍妇!
我要去衙门告你!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的恶行!”霍无双端起桌上的一盘花生米,
往嘴里扔了一颗,嚼得嘎嘣脆。“休书?”她笑了笑,“行啊。不过在写休书之前,
咱们得先算算账。”她拍了拍手。门外立刻走进来了两个账房先生,
手里捧着比砖头还厚的账本。“念。”账房先生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,清了清嗓子,
开始报账。“宣德三年五月,柳知远支取白银五百两,名目:修缮书房。实则购入古琴一张,
赠予醉香楼头牌小桃红。”“宣德三年六月,柳知远支取白银八百两,名目:赈灾。
实则购入前朝孤本《金瓶梅》一套。”“宣德三年八月,柳知远支取白银一千两,
名目:打点上司。实则为表妹林黛柔置办头面首饰三套,
苏绣罗裙十件……”随着账房先生那毫无起伏的声音,柳知远的脸色越来越白,
最后变得惨白如纸。林黛柔更是缩成一团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“够了!别念了!
”柳知远大吼一声,试图打断这公开处刑,“这……这都是为了这个家!我是为了结交权贵!
为了咱们的未来!”“未来?”霍无双站起身,走到柳知远面前。她每走一步,
柳知远就往后缩一步。“柳知远,你是不是觉得,老娘在边关杀人,你在家里花钱,
是天经地义的事?”霍无双的声音很轻,却透着一股子让人骨头缝里发寒的冷意。“这三年,
霍家军阵亡将士的抚恤金,朝廷发下来一共三万两。我怎么听说,这笔钱,也没了?
”柳知远的瞳孔猛地一缩。“那……那是……”他结结巴巴,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,
“那是借出去了!对!借给同僚周转了!很快就还!”“借给谁了?”霍无双逼视着他,
“是借给东城的赌坊了,还是借给西城的窑子了?”柳知远双腿一软,直接瘫坐在了地上。
他没想到,霍无双竟然查得这么清楚。“你……你监视我?”“监视你?”霍无双嗤笑一声,
“对付你这种货色,还需要监视?派个斥候去街上随便打听打听,
你柳大官人的‘风流韵事’,都能编成评书连讲三天三夜不带重样的。”她蹲下身,
用刀鞘拍了拍柳知远的脸。“柳知远,你把老娘当傻子哄,这不叫兵不厌诈,这叫自寻死路。
”4见柳知远彻底哑火了,林黛柔知道,自己再不出手,这长期饭票就要飞了。她咬了咬牙,
决定使出杀手锏。“姐姐!”林黛柔突然扑过来,跪在霍无双脚边,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,
闻者伤心,听者流泪。“千错万错,都是柔儿的错!是柔儿身子骨弱,表哥才多照顾了一些。
姐姐要打要罚,就冲着柔儿来吧!千万别怪罪表哥,气坏了身子不值当啊!
”这一招“以退为进”,在宅斗界可是屡试不爽的绝学。一般的大妇,
遇到这种看似柔弱、实则道德绑架的招数,往往会被气得七窍生烟,却又发作不得,
否则就落了个“妒妇”的名声。可惜,她遇到的是霍无双。霍无双是个粗人。粗人解决问题,
从来不走心,只走肾……啊不,只走力。“既然知道错了,那就好办。”霍无双点了点头,
一脸“我很讲道理”的表情。“王铁柱!”“在!”“按军法,私吞军饷、动摇军心者,
该当何罪?”王铁柱大声吼道:“斩立决!”林黛柔的哭声戛然而止,
像是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。斩……斩立决?这剧本不对啊!不是应该骂我两句,
然后我再哭两声,最后表哥心疼我,咱们再拉扯三百回合吗?怎么上来就要砍头?
“念你是初犯,且非军中之人,死罪可免。”霍无双慢条斯理地说着,林黛柔刚松了一口气,
就听见下一句:“活罪难逃。来人,拖下去,重打八十军棍。打完了扔出府去。
”“八……八十?”林黛柔两眼一翻,差点直接晕过去。八十军棍?那是打男人的!
她这娇滴滴的身子骨,八棍子下去估计就成肉泥了!“姐姐!饶命啊!表哥!救我!
”林黛柔死死抱住柳知远的大腿,哭得撕心裂肺。柳知远也被吓傻了。他知道霍无双狠,
但没想到她这么狠。“无双!你疯了!这是私刑!你这是草菅人命!
”柳知远试图用大道理压她,“这里是京城!是天子脚下!不是你的边关大营!
”“天子脚下?”霍无双站起身,环顾四周。“这宅子,是圣上赐给我的。这府里的规矩,
就是我霍无双的规矩。”她指了指大门口。“在这个院子里,老娘就是天。
”两个五大三粗的亲兵走上前,像拖死狗一样,把林黛柔拖了下去。不一会儿,
外面就传来了“噼里啪啦”的板子声,和林黛柔鬼哭狼嚎的惨叫声。柳知远听着那声音,
每一板子都像是打在他心尖上。但他不敢动。因为霍无双的那把刀,正架在他的脖子上。
刀锋冰凉,激起了他一身的鸡皮疙瘩。“现在,轮到你了。”霍无双看着他,
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“我的钱,花得爽吗?”5柳知远咽了口唾沫。
他感觉自己的脖子随时都会和脑袋分家。“无……无双,
一日夫妻百日恩……”他试图打感情牌,声音抖得像筛糠,“我……我以后改!我一定改!
钱……钱我会想办法还上的!”“还?你拿什么还?”霍无双冷笑,
“拿你那些不值钱的破字画?还是拿你那颗猪脑子?”她收回刀,反手就是一巴掌。“啪!
”这一巴掌,清脆响亮,直接把柳知远打得原地转了三圈,半边脸瞬间肿得像个发面馒头。
“这一巴掌,是替那些战死的兄弟打的。他们的卖命钱,你也敢动!”柳知远被打懵了,
捂着脸,嘴角流血,眼神涣散。“啪!”反手又是一巴掌。“这一巴掌,
是替霍家列祖列宗打的。招了你这么个玩意儿进门,真是祖坟冒青烟——倒了八辈子血霉!
”柳知远两眼冒金星,感觉天旋地转。“啪!”第三巴掌。“这一巴掌,是替孔夫子打的。
读了那么多圣贤书,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?仁义礼智信,你占了哪一样?除了吃喝嫖赌,
你还会什么?”三巴掌下去,柳知远彻底变成了猪头。他瘫在地上,连哼哼的力气都没了。
霍无双掏出一块帕子,嫌弃地擦了擦手,然后把帕子扔在柳知远脸上。“王铁柱。”“在!
”“把这玩意儿给我绑了,吊在府门口的旗杆上。”霍无双淡淡地吩咐道,
“写个牌子挂他脖子上,就写:‘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柳大人卖身还债,一文钱摸一次,
十文钱踹一脚。所得款项,全部充入抚恤金。’”王铁柱眼睛一亮:“好嘞!大将军,
这主意绝了!俺这就去办!”柳知远听完,两眼一翻,彻底晕了过去。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啊!
读书人的脸面,这下子算是彻底被踩进泥里,还要被万人践踏了。
霍无双看着像死猪一样被拖走的柳知远,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爽吗?有点。但这还不够。
这只是个开始。她霍无双失去的东西,不仅要拿回来,还要连本带利地讨回来。“传令下去。
”霍无双对着空荡荡的院子说道。“把这府里里外外,给我用开水烫三遍。尤其是那张床,
给我劈了当柴烧。”她嫌脏。柳知远被挂在旗杆上晃悠了半个时辰。日头毒辣,
晒得他那张猪头脸油光锃亮。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,铜板扔了一地,叮叮当当的,
听着倒是比他作的那些酸诗悦耳。就在王铁柱准备收第二轮“参观费”的时候,
街口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嚎叫。“我的儿啊!天杀的!这是要绝了我老柳家的后啊!
”一辆租来的青布马车停在了府门口。车帘子一掀,
滚下来一个穿着大红寿字纹对襟褂子的老太婆。这是柳知远的亲娘,柳老太太。
当初柳知远入赘霍家,这老太太死活不愿意住进来,说是寄人篱下丢了祖宗脸面,
一直住在城郊的老宅里。如今听说儿子发达了,正准备搬进来享清福,没成想刚到门口,
就看见自己的宝贝疙瘩像条腊肉似的挂在天上。柳老太太两眼一翻,拍着大腿就坐在了地上。
“霍无双!你个杀千刀的扫把星!你克死了爹娘不算,现在还要谋害亲夫!我要去告御状!
我要让皇上评评理!”她一边嚎,一边拿脑袋往石狮子上撞。当然,撞得很有分寸,
雷声大雨点小,连油皮都没蹭破。霍无双正坐在门房里喝茶。听见动静,她放下茶盏,
提着马鞭走了出来。“哟,这不是婆母吗?”霍无双笑了笑,那笑容里没有半点温度,
“怎么,今儿个是什么好日子,您老人家不在乡下纳鞋底,跑到本将军的辕门外唱大戏?
”柳老太太见正主出来了,立马从地上弹了起来。她仗着自己是长辈,
张牙舞爪地就往霍无双脸上挠。“你个不守妇道的泼妇!快把我儿放下来!
不然老娘今天就撞死在你面前!”霍无双没躲。她身上还穿着那身黑铁甲胄。
柳老太太的九阴白骨爪“咔嚓”一声,抓在了护心镜上。指甲劈了。“哎哟!我的手!
杀人啦!儿媳妇打婆婆啦!”柳老太太疼得直跳脚,捂着手指头,哭得更凶了。霍无双低头,
弹了弹护心镜上并不存在的灰尘。“婆母,这是御赐的宝甲,刀枪不入。您这肉体凡胎的,
就别拿鸡蛋碰石头了。”她转过身,对着王铁柱挥了挥手。“既然婆母来了,那就请进去吧。
正好,我这儿还有笔账,得跟您老人家好好算算。”6柳知远终于被放了下来。
他已经没了人样,被两个亲兵架着,像拖死狗一样拖进了正厅。柳老太太跟在后面,一进屋,
眼睛就直了。原本摆在多宝阁上的那些古董花瓶、玉石摆件,全都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,
是一排排寒光闪闪的兵器架。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。正厅中央,
原本挂着柳知远亲笔题写的“宁静致远”横幅,现在换成了一张巨大的老虎皮。
那老虎张着血盆大口,眼珠子瞪得溜圆,正对着门口。柳老太太吓得腿一软,差点跪下。
“这……这是家里,还是阎王殿啊?”霍无双坐在虎皮椅上,手里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姜汤。
“婆母,坐。”她指了指下首的一张太师椅。那椅子上铺着一层带刺的狼牙棒……啊不,
是一层硬邦邦的竹席。柳老太太哪敢坐,只能站在柳知远身边,抹着眼泪。“无双啊,
知远他纵有千般不是,那也是你的天。你这么折腾他,就不怕遭雷劈吗?”“雷劈?
”霍无双放下碗,“雷公电母挺忙的,估计没空管这种闲事。倒是您老人家,
这三年从将军府搬走的东西,是不是该吐出来了?”柳老太太脸色一变,眼神开始飘忽。
“什……什么东西?我一个老婆子,能拿你什么东西?”“王铁柱,念。
”王铁柱又掏出了那本账册。“宣德三年九月,柳老太太以‘做寿’为名,
从库房支取南海珍珠一斛,价值八百两。”“宣德四年正月,柳老太太以‘身体抱恙’为名,
支取百年老参三支,价值一千二百两。”“宣德四年六月,柳老太太搬走紫檀木罗汉床一张,
说是腰疼,要睡硬床……”随着一桩桩一件件被抖落出来,柳老太太的脸色由白转红,
又由红转青。“胡说!这都是胡说!”柳老太太开始撒泼,“那是知远孝敬我的!
儿子孝敬娘,天经地义!你算哪根葱,敢管我们娘俩的事?”“儿子孝敬娘,确实天经地义。
”霍无双点了点头,“但前提是,那得是儿子自己挣的钱。柳知远这个废物,
连自己都养不活,拿我的军饷去充孝子,这叫‘借花献佛’?不,这叫‘慷他人之慨’,
叫‘偷’。”她猛地一拍桌子。“限你三日之内,把东西全部送回来。少一个子儿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