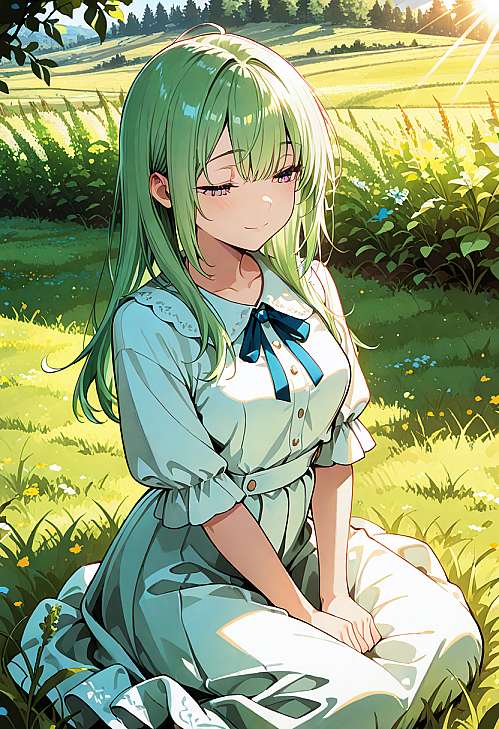我叫沈婉,是当朝最受宠的惠妃沈眉君的孪生妹妹。我们自幼分离,她养在京城,
我被送去神医谷学医。我苦学十年,终成一代毒医,只为能入宫保护她。
可我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,竟是她难产血崩的死讯。他们说,姐姐是福薄。我笑着撕了信,
背上我那装着一百零八种奇毒的药箱。福薄?那我便让这整个后宫,乃至前朝,
都来给姐姐的“福薄”殉葬!他们说姐姐死于难产,可我却在她腕间,摸到了七日绝的脉息。
而那个被姐姐临终托付,哭得肝肠寸断的好姐妹,莞贵人苏玉嬛,
指甲缝里却藏着极难察觉的催产草药残渣。1京城的风,吹不起神医谷的半分尘埃。
可姐姐的死讯,却像一把淬了冰的刀,隔着千里,捅进我的心口。信纸上,
皇帝的朱笔御批写着“天妒红颜,福薄命舛”,字字透着伪善的惋惜。福薄?
我那自幼便被相士批命“贵不可言”的姐姐,会是福薄?我撕了信,将碎片碾进香炉。
青烟袅袅,像极了姐姐临终前不甘的魂。我叫沈婉,姐姐叫沈眉君。我们是孪生姐妹,
她端庄娴雅,养在深闺,是家族的荣耀。我离经叛道,远赴神医谷,是家族不愿提及的禁忌。
我们约定,待我医毒双绝,便入宫做她的臂膀,护她一世周全。可我等来的,
是她的一口薄棺。半月后,我跪在惠妃灵前,一身缟素。皇帝玄凌一身明黄,站在我身侧,
叹息着。“婉儿,你与眉君生得真像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病态的迷恋,
目光在我脸上流连,像是在透过我,看另一个人。“只可惜,眉君她……福薄。
”又是这两个字。我垂下眼,掩去所有情绪,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。“臣女想单独,
再陪陪姐姐。”他沉默片刻,终是应允。空旷的灵堂里,只剩下我和姐姐冰冷的棺椁。
我推开沉重的棺盖。姐姐安静地躺在里面,妆容精致,仿佛只是睡着了。可那张脸,
却透着死气的青白。我的指尖搭上她冰冷的手腕。三指之下,一片死寂。我闭上眼,
将毕生所学凝聚于指尖,一寸寸探寻那早已消散的脉息。有。在腕骨深处,
藏着一丝若有似无的迟滞感。是“七日绝”。一种极为阴毒的慢性毒药,无色无味,
每日微量,七日便可耗尽心血,神仙难救。发作时,与难产血崩的症状,一模一样。我的心,
一寸寸冷下去。我掀开姐姐的衣袖,手臂内侧,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细小针孔。七日绝,
需以特制的牛毛细针,日日刺入血脉。是谁,能日日近她的身,还能让她毫无防备?
我的目光,落在姐姐紧攥的右手上。我一根根掰开她僵硬的手指,掌心里,
是一块被汗水浸透的玉佩。玉佩上,刻着一个“嬛”字。莞贵人,苏玉嬛。
姐姐在信中提过无数次的好姐妹,在她难产时“尽力相助”,哭得肝肠寸断的知己。
我死死攥住那块玉佩,玉石的棱角硌得我掌心生疼。好一个姐妹情深。我站起身,
深深看了一眼姐姐安详的睡颜。“姐姐,等我。”“很快,我就送他们下来,给你赔罪。
”2我以“为姐姐守灵祈福”为由,留在了宫里。皇帝欣然应允,
将我安置在离他养心殿不远的碎玉轩,那是姐姐从前最爱去的地方。他日日召我过去说话,
赏赐流水般地送来。所有人都说,沈家二小姐要走惠妃的老路,靠着一张相似的脸,
再获圣宠了。我只是笑。太后召见了我。她端坐在高位,满脸慈爱地拉着我的手。“好孩子,
眉君的事,你也别太伤心了。”“往后,就把这宫里当自己家。”她身边的安陵容,
那个总是怯生生跟在姐姐身后的安常在,正低眉顺眼地为她捶着腿。我注意到,
她新做的护甲上,描着精致的丹蔻。姐姐尸骨未寒,她倒是有心情打扮自己。
“多谢太后娘娘垂怜。”我恭顺地回话。席间,苏玉嬛也来了。她一身素雅宫装,眼眶微红,
见到我,眼泪就先落了下来。“婉妹妹,见到你,我就想起眉姐姐……”她拉着我的手,
情真意切,仿佛悲痛欲绝。我任由她握着,指尖却在她微凉的掌心轻轻一划。很好,
心率不齐,气息虚浮。这是长期接触“催产草”后,对自己身体造成的损伤。
我面上不动声色,心中却已是杀意翻腾。“苏姐姐节哀,姐姐泉下有知,
也不愿看你如此伤心。”一场虚情假意的会面结束。我回到碎玉轩,开始清点我的药箱。
一百零八种奇毒,每一种,我都为它们想好了归宿。第一个,就从安陵容开始。
她不是最爱惜她那副嗓子么?那我就让她,再也唱不出来。我很快就找到了机会。
安陵容为了固宠,每日都要练习嗓音,喝大量的枇杷露润喉。我借着去太后宫里请安的机会,
“偶遇”了她。“安姐姐,你这嗓子,听着有些沙哑。”我故作关切,取出一个瓷瓶。
“这是家师特制的‘玉露琼浆’,以天山雪莲和百种花蜜制成,最是润喉养声。
姐姐若不嫌弃,不妨一试。”安陵容看着我,眼神里带着一丝戒备和探究。
她当然不会轻易相信我。我拔开瓶塞,自己先抿了一口,微笑道:“姐姐放心,无毒。
”她犹豫片刻,终究是抵不过那副金嗓子的诱惑,接了过去。“多谢婉妹妹。”她不知道,
“玉露琼浆”本身确实无毒,甚至是大补之物。可一旦遇上她每日必喝的枇杷露,
就会化作一副无解的哑药。药效不会立刻发作,而是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,
一点点侵蚀她的声带。等她发现时,一切都晚了。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,嘴角的笑意,
冰冷刺骨。安陵容,你只是个开始。3皇帝的寿宴上,安陵容被推了出来献唱。
她穿着一身水绿色的罗裙,抱着琵琶,袅袅婷婷地走到台前。一开口,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那曾经如黄莺出谷般婉转的歌喉,此刻却像是被砂纸磨过一般,干涩,嘶哑,
甚至还带着几分破锣似的音。她唱得极其吃力,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,一张小脸涨得通红。
玄凌的脸色,瞬间阴沉下来。“放肆!”他一摔酒杯,金樽落地,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“此等靡靡之音,也敢在朕的寿宴上聒噪!”安陵容吓得魂飞魄散,当场跪倒在地,
琵琶摔在一旁,琴弦断裂,发出“铮”的一声哀鸣。“皇上饶命!皇上饶命!
臣妾……臣妾也不知道是怎么了……”她想为自己辩解,可一开口,
那难听的嗓音就让玄凌更加厌恶。“拖下去!禁足于延禧宫,无朕旨意,不得出宫门半步!
”安陵容被人像拖死狗一样拖了下去,哭喊声渐渐远去。我端着酒杯,
轻轻晃动着里面琥珀色的液体,唇边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。坐在我身边的苏玉嬛,
脸色有些发白。她看向我的眼神,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。我知道,她开始怕了。
这就对了。猫捉老鼠的游戏,要慢慢玩,才有趣。寿宴不欢而散。当晚,
玄凌来了我的碎玉轩。他喝了很多酒,眼神迷离,一把握住我的手。“婉儿,只有你,
只有你最像她。”他把我当成了姐姐的替身。我没有挣扎,顺从地靠在他怀里,声音轻柔。
“皇上,姐姐若在,看到您为她如此伤神,定会心疼的。”我提起姐姐,
他的眼神便柔和下来。“是啊,眉君她,总是那么体贴。”我抬起头,直视着他的眼睛。
“皇上,臣女有个不情之请。”“说。”“安常在的嗓子,似乎是中了什么邪祟,
臣女略通医理,想去为她瞧瞧,也算是为姐姐积福。”玄凌皱了皱眉,
显然对安陵容已经毫无兴趣。但他看着我这张酷似沈眉君的脸,终究还是点了点头。“准了。
”得到许可,我立刻去了延禧宫。安陵容正坐在地上,披头散发,形同疯妇。看到我,
她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,连滚带爬地扑过来。“婉妹妹!救我!你一定有办法的,对不对?
”我扶起她,故作怜悯地叹了口气。“姐姐别急,我先为你把把脉。
”我的手指搭在她的腕上,片刻后,我收回手,面色凝重。“姐姐,你这不是病,是毒。
”安陵容的脸,瞬间血色尽失。“毒?谁?是谁要害我?”我看着她惊恐的眼睛,一字一句,
缓缓说道。“下毒之人,手法极其高明,此毒……与姐姐你平日里用的香料有关。
”我特意加重了“香料”二字。安陵容的身体,猛地一僵。4安陵容最擅长的,便是调香。
她曾用特制的“迷情香”固宠,也曾用相克的香料,害得富察贵人小产。这些事,
她做得极为隐秘。如今被我一语道破,她眼中的惊恐,几乎要溢出来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会知道……”“我知道的,远比你想象的要多。”我凑到她耳边,
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,轻声说。“比如,惠妃娘娘难产那日,
你送去的那盆促进宫缩的‘依兰’。”安-陵-容-的-瞳-孔-骤-然-紧-缩。
她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鸡,浑身颤抖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“你……你胡说!
”她终于挤出几个字,声音却虚弱得毫无说服力。“我胡说?”我冷笑一声,
从袖中取出一枚银针,在她眼前晃了晃。“安姐姐,我这银针,不仅能救人,
也能让人……说实话。”“神医谷的催眠术,你想不想试试?”她看着我,
像在看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恐惧彻底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。她瘫倒在地,泣不成声。
“不是我……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……”“是皇后……是皇后娘娘让我这么做的!
”“她说惠妃家世显赫,若诞下皇子,必会威胁到大皇子的地位,她说事成之后,
会保我一世荣华……”“还有苏玉嬛!她嫉妒惠妃盛宠,嫉妒她家世比自己好!那碗催产药,
就是她亲手端过去的!”原来如此。原来是三方合谋。一个出谋,一个动手,一个递刀。
我可怜的姐姐,到死都不知道,自己身边,竟围了三条毒蛇。“我……我说的都是真的!
”安陵容见我沉默,急切地抓住我的衣角。“求求你,
放过我……我只是个棋子……”“棋子?”我一脚踢开她,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
“姐姐被你们害死的时候,你怎么不说自己是棋子?
”“你享受着踩着她的尸骨换来的荣华时,怎么不说自己是棋-子?”我蹲下身,
捏住她的下巴,强迫她看着我。“安陵容,你听好了。”“你的嗓子,是我毁的。
”“你放心,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地死。”“我会让你,在无尽的惊恐和绝望中,
一点点烂掉,就像你那颗肮脏的心一样。”说完,我站起身,不再看她一眼,转身离去。
身后,是她歇斯底里的尖叫和哭嚎。几天后,宫里传出消息。安常在疯了。她逢人就说,
是皇后和莞贵人害死了惠妃。她还说,自己宫里有鬼,是惠妃的冤魂回来索命了。起初,
没人相信一个疯子的话。直到有一天,侍卫在延禧宫的墙角下,挖出了一个布偶。布偶上,
写着惠妃的生辰八字,身上插满了密密麻麻的钢针。人证物证俱在。用巫蛊之术诅咒宫妃,
是株连九族的大罪。玄凌大怒,下令彻查。很快,安陵容当年用香料害富察贵人小产的旧事,
也被翻了出来。罪上加罪。玄凌下旨,废黜安陵容位份,赐毒酒一杯。
我特意去“送”了她最后一程。她被两个太监按在地上,形容枯槁,眼神呆滞。看到我,
她才有了些反应,挣扎着,嘴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声响。我走到她面前,蹲下身。“安陵容,
我给你准备的这杯酒,叫‘穿肠’。”“喝下去,不会立刻死,
你的五脏六腑会像被蚂蚁啃噬一样,一点点腐烂,这个过程,会持续三天三夜。
”“好好享受吧,这是你应得的。”我看着她眼中迸发出极致的恐惧,
看着她被人强行灌下那杯黑色的毒酒。我笑了。姐姐,看到了吗?第一个,已经上路了。
5.安陵容的死,像一块石头投入湖中,激起了层层涟漪。苏玉嬛变得愈发谨慎。
她开始称病,闭门不出,拒绝一切入口的东西。她以为这样,我就拿她没办法了。天真。
我要毁掉一个人,何须用毒?我要诛她的心。苏玉嬛最在乎的,无非是两样东西。
一是玄凌的宠爱,二是她的家世。那我就让她,一样样失去。我开始频繁地出入养心殿。
有时是陪玄凌下棋,有时是为他抚琴。我从不邀宠,也从不提及前朝后宫。
我只是安静地陪着他,在他批阅奏折疲惫时,递上一杯安神茶;在他因朝事烦心时,
为他弹一曲清心普善咒。我学着姐姐的样子,温柔,体贴,却又带着一丝疏离。
玄凌愈发沉溺于这种感觉。他看我的眼神,从最初的迷恋,渐渐多了一丝依赖。
他开始留我在养心殿过夜,但从不碰我。他只是喜欢在深夜,拥着我,
呢喃着“眉君”的名字入睡。整个后宫都看在眼里。她们嫉妒我,却又无可奈何。
因为我是沈眉君的妹妹,因为我只“侍寝”,不“承宠”。苏玉嬛坐不住了。
她精心打扮了一番,端着一碗莲子羹,去了养心殿。彼时,我正在为玄凌磨墨。她进来时,
玄凌正握着我的手,教我写他的名字。那姿态,亲昵得像一对璧人。苏玉嬛的脸,
当场就白了。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“皇上,臣妾炖了您最爱喝的莲子羹。”玄凌头也没抬,
淡淡地说:“放下吧。”苏玉嬛的笑容,僵在脸上。她不甘心,又转向我。“婉妹妹也在啊,
妹妹真是好福气,能时时伴在君侧。”话里藏着针。我抬起头,对她露出一个无害的笑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