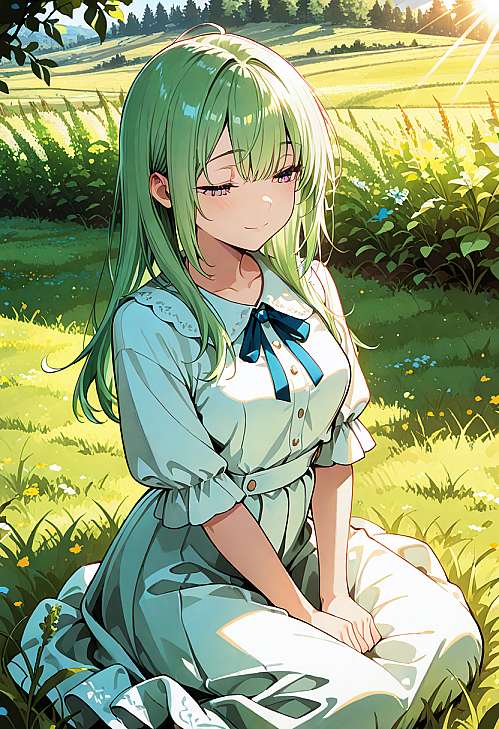寒夜茶花落得如雪,我跪在微凉的玉阶上,看着曾许我一世安稳的人,
将一杯暗有毒气的茶递到我面前。我是云家嫡女云舒晚,三日之前,家门尚在,父兄安康,
婚约在身,满城艳羡。我倾心相待的人,是如今步步登天的裴夜寒,我以为是情深,
到头来却是一场屠门的局。火光烧红夜空时,我才知道,所有温柔都是铺垫,
所有亲近都是算计。他要的从不是我,是云家手握的秘务与权柄,是踩着我满门尸骨,
往上攀爬的阶梯。我那一向温顺的庶妹云怜月,依偎在他身侧,笑得柔弱又恶毒。
她说我占了太久的风光,该把一切都让给她。裴夜寒看着我,眼神淡漠如冰。“云舒晚,
你家罪证确凿,喝了这杯,我留你全尸。”我没有接,反手将茶泼在地上,
青石瞬间泛起一层黑雾。“你给的爱,从一开始就是毒。”下一刻,剧痛刺穿心口,
那只他日日送我佩戴的茶花香囊,早已浸了慢性奇毒。我从玉阶滚落,意识消散前,
只听见他冷冷吩咐,将我丢去乱葬岗。黑暗吞没我的刹那,胸口祖传的茶花玉坠骤然发烫,
一股清冽而霸道的力量涌入四肢百骸。那是云家不传之秘,唯有历经挚爱背叛、濒死重生,
方能觉醒。我能辨天下毒,能制天下毒,亦能以花香为引,无声夺魂。再次睁眼,
我躺在尸骸之间,月色惨白,茶花香气自指尖漫开。我从地狱爬回来了。裴夜寒,
你赠我一场毒爱,我便还你一整座地狱。我隐匿在夜色中,抹去脸上血污,
将散乱的发丝挽起,遮住眉心那一点浅淡的茶花印记。乱葬岗外有车马声响,
是裴夜寒的人在确认我的死讯,我敛去所有气息,如同暗夜孤魂,待他们离去,
才悄无声息踏入回城的路。乱葬岗与京城相隔数十里,一路荒草萋萋,寒风吹过林间,
发出呜咽般的声响,像是无数枉死之人的泣诉。我赤脚走在冰冷的泥土上,碎石划破脚底,
渗出血迹,每一步都带着刺痛,可这点痛,比起心口的万分之一,根本不值一提。
我曾是锦衣玉食、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女,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出门必有车马相随,
身边丫鬟仆从成群,从未受过半分委屈。可一夜之间,我失去所有,沦为丧家之犬,
被最爱的人背叛,被最亲的妹妹算计,连一具全尸都不配拥有。天边泛起鱼肚白时,
我终于抵达京城外的护城河。河水清澈,倒映出我狼狈不堪的模样,白衣染血,发丝凌乱,
脸上布满尘土与泪痕,早已没了往日半分风华。我俯身捧起河水,一点点清洗脸上的污痕,
看着水中那双不再有半分温柔,只剩寒戾与决绝的眼眸,我知道,
从前那个天真软弱的云舒晚,真的死了。从今往后,我只为复仇而活。城门开启,
百姓与商贩陆续入城,我混在人群之中,低着头,用衣袖遮住半张脸,顺利进入京城。
城内依旧繁华如旧,街道两旁商铺林立,酒旗迎风招展,叫卖声、谈笑声此起彼伏,
一派热闹祥和之景。可这份繁华之下,却藏着最肮脏的阴谋与最血腥的罪孽。
云家满门四十七口,一夜之间尽数殒命,府邸被查封,家产被抄没,所有与云家交好的势力,
纷纷撇清关系,生怕引火烧身。世人皆道云家谋逆叛国,罪有应得,却无人知晓,
这一切都是裴夜寒与云怜月精心编织的谎言。我沿着长街慢行,
目光平静地扫过一座座高门府邸,将朝中各方势力的分布、立场、恩怨,一一记在心底。
云家执掌京城防卫多年,父兄在军中与朝堂皆有旧部,只是如今群龙无首,又被裴夜寒打压,
早已四分五裂,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不能贸然联系他们,一旦暴露身份,不仅自身难保,
还会将那些尚存良知的旧部推入绝境。我需要一个全新的身份,一个足够隐蔽,
又能接近权力中心的身份。行至朱雀大街,一辆鎏金雕花马车缓缓驶过,护卫森严,
路人纷纷避让,眼中满是敬畏。车帘被风掀起一角,我清晰地看见,裴夜寒端坐其中,
一身紫袍,腰束玉带,面容俊朗,意气风发。他的身边,
依偎着妆容精致、头戴珠翠的云怜月,两人相视而笑,模样登对,刺得我眼睛生疼。
那本该是我的位置,本该是我的人生,却被他们用鲜血与阴谋,生生夺走。
指甲深深掐入掌心,渗出血丝,我强迫自己移开目光,将滔天恨意压在心底。不急,
我有的是时间。我要看着他们爬上最高处,再亲手将他们推入深渊,
让他们尝遍我所受的所有痛苦,让他们为云家四十七口亡魂,血债血偿。
我在京城最偏僻的西巷,寻到一处废弃的小院。小院不大,只有一间正房与一间偏房,
院墙斑驳,院内杂草丛生,却胜在隐蔽,四周邻居皆是普通百姓,极少与人往来,
正好方便我暗中行事。我简单收拾了一番,扫去屋内的灰尘,用干草铺成简易的床榻,
就算有了安身之处。接下来的数日,我足不出户,日夜静心感受体内觉醒的力量,
熟悉茶花玉坠带来的秘能。我发现,这股力量远比我想象中更加强大。我能凭借一缕花香,
探知方圆十里内的所有动静,风吹草动、人声低语,
都清晰地传入耳中;我能轻易分辨出食物、茶水、香料中任何一丝异样,
哪怕是最隐蔽的慢性毒药,也逃不过我的感知;我能以白茶花为引,布下迷阵、惑人心神,
甚至能在无形之中,让人身中奇毒,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。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复仇利器,
是云家亡魂护佑我的力量。我开始利用院中生长的野草与野花,调配最简单的迷药与毒粉,
反复练习操控花香的技巧,直到运用自如,收发由心。与此同时,我也在暗中打探消息,
听巷间百姓议论,听往来商贩闲谈,将裴夜寒与云怜月的近况,一一记在心里。
裴夜寒因剿灭“谋逆”的云家有功,被陛下破格提拔,封为镇北将军,执掌部分京城兵权,
成为朝中最炙手可热的新贵。云怜月则以云家庶女的身份,被裴夜寒明媒正娶,接入将军府,
成为人人艳羡的将军夫人。他们踩着我云家的尸骨,享受着无上荣光,夜夜笙歌,好不风光。
而我,在阴暗的小院里,日夜与恨意相伴,打磨着复仇的利刃。第七日夜里,我终于出手。
我趁着夜色,悄无声息潜入将军府。府内守卫森严,灯火通明,处处可见巡逻的护卫,
可在我的花香迷阵之下,所有护卫都变得昏昏沉沉,眼神呆滞,根本无法察觉我的踪迹。
我一路畅通无阻,来到云怜月居住的汀兰院。院内种满了白茶花,与我云家旧院一模一样,
显然是云怜月故意为之,想要模仿我的模样,取代我的存在。屋内灯火通明,
传来云怜月娇柔的笑声,与丫鬟们说着闲话。“夫人如今真是好福气,嫁给了将军,
又成了京城最尊贵的夫人,那云舒晚要是地下有知,怕是要气得活过来。”“活过来又如何?
还不是死在将军手里,她那满门都成了亡魂,再也翻不了身了。”云怜月轻笑一声,
语气满是得意与恶毒:“她本来就不配与将军相配,云家也不配拥有那般权势,
如今一切都归我,是她活该。”我站在窗外,指尖的茶花香气缓缓渗入屋内。
这是我调配的第一种奇毒,无臭无味,不会立刻发作,却会让人浑身奇痒难忍,肌肤溃烂,
日夜不得安宁,寻常名医根本无法诊治。这是我送给她的第一份礼物。做完这一切,
我没有丝毫停留,悄无声息退出将军府,回到自己的小院。次日清晨,将军府便乱作一团。
云怜月一夜之间身染怪疾,浑身瘙痒不止,肌肤泛起大片红疹,抓得血肉模糊,痛不欲生。
裴夜寒震怒,遍请京城所有名医前来诊治,可所有大夫都束手无策,纷纷摇头离去,
无人能说出病因,更无人能解开此毒。一时间,将军府人心惶惶,流言四起。有人说,
是云家冤魂不散,前来索命;有人说,是裴夜寒杀戮过重,遭了天谴;还有人说,
是将军府风水不好,招惹了邪祟。裴夜寒本就生性多疑,杀伐果断,如今府中怪事频发,
更是草木皆兵,整日焦躁不安,派人四处寻访奇人异士,想要治好云怜月,
想要平息府中的诡异之事。可他派出去的人,要么莫名迷路,要么突发怪病,要么一去不回,
没有一个能顺利带回有用的消息。我坐在小院里,听着窗外传来的议论声,
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这不是天谴,这是我,从地狱归来,亲手降下的惩罚。
他们欠我的,才刚刚开始偿还。就在京城众人对将军府的怪事议论纷纷之时,
一位神秘的医女,悄然出现在京城之中。这位医女性情清冷,容貌绝美,医术卓绝,
能解世间各种疑难杂症,更能化解各种诡异奇毒,短短数日,便在京城声名鹊起。
无人知晓她的来历,无人知晓她的姓名,只知道她独居在西巷小院,轻易不接诊,
可只要她出手,便没有治不好的病。这位医女,便是我。我易容改貌,改变了身形与气质,
用一方轻纱遮住半张脸,以全新的身份,出现在世人面前。
我接连为几位权贵诊治好了久治不愈的顽疾,名声越来越大,很快便传到了裴夜寒的耳中。
不出所料,当日下午,将军府的管家便带着重金,来到我的小院,恳请我前往将军府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