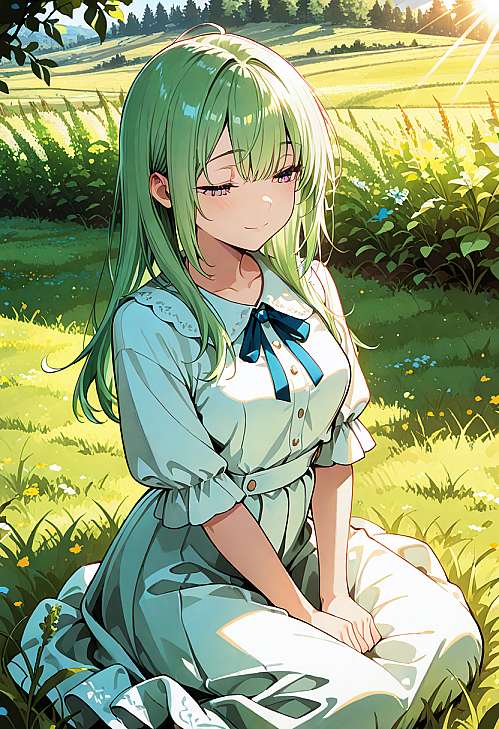我是当朝最贤良的太子妃,直到太子带回来一个穿越女。她说人人平等,骂我封建糟粕,
还设计让我在宫宴上跳艳舞。我哭着说这是莫大屈辱时,太子搂着她嘲笑我假正经。
后来我爹起兵了,穿越女惊恐地问为什么冷兵器能打赢她的火药。
我随手扔掉滴血的长枪:“介绍一下,我娘是穿越的,我爹是重生的。
”“而本宫——装贤良装了十年,终于不用再演了。”---我,沈知微,当朝太子妃,
今天也很贤良。卯时三刻,天还黑着,我已经穿戴整齐,坐在铜镜前由着丫鬟梳头。
镜子里的人眉眼温顺,唇角噙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弧度,连头发丝儿都透着“规矩”二字。
贴身侍女秋云手脚麻利,嘴里也不停:“娘娘,今儿十五,各宫娘娘们都要来请安,
您看是先用些点心垫垫,还是等请安后再传膳?”“等人齐了再说,莫失了礼数。
”我声音不高不低,透着晨起的温润,眼风扫过妆台上那支赤金点翠凤钗——皇后昨日赏的,
嘱我今日务必戴上,彰显太子妃的体面。我瞧着那钗,凤眼镶着两粒小小的红宝,
赤金在烛光下有些刺目。贤良的太子妃,自然要时时体察上意,哪怕这凤钗沉得能压断脖子。
宫门次第而开,沉寂的东宫苏醒过来,脚步声、低语声、器物轻碰声,
汇成一股沉闷的、不容出错的音流。我起身,理了理身上繁复的宫装,
那上面用金线绣着大朵大朵的牡丹,富丽堂皇,却也死气沉沉。请安的流程乏善可陈。
良娣、承徽、昭训……环肥燕瘦,花团锦簇,带着格式化的笑容和言语,
像是同一口窑里烧出来的瓷人儿。我挂着万年不变的温和笑意,接受她们的叩拜,
说些“姊妹和睦”、“尽心侍奉”的场面话,赏些不轻不重的玩意儿。
空气里弥漫着脂粉香和一种更深沉的、名为“争宠”的暗流,粘稠得让人呼吸不畅。
直到那位林良媛出现。她几乎是掐着最后的点儿进来的,穿着一身水碧色的裙子,
式样简单得近乎失礼,头发也只松松挽了个髻,插了根玉簪。在一群珠翠环绕的嫔妃里,
她素净得扎眼。行礼也敷衍,膝盖弯得不够深,眼皮甚至抬起来,直直看了我一眼。
那眼神里没有敬畏,也没有讨好,只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打量,甚至带着点……怜悯?
“妾身林月儿,给太子妃娘娘请安。”声音倒是清脆,只是语调平平,听不出多少敬意。
满屋子霎时一静。所有人都低了头,眼角余光却像钩子一样挂在她身上。
我脸上的笑容分毫未变,温声道:“林良媛来了,入座吧。秋云,看茶。”她落座,
接过茶盏,喝了一口,眉头就皱起来:“这茶……味儿不对吧?像是陈了。”秋云脸色一变。
我抬手止住她,依旧笑着:“今年新进的雨前龙井,许是林良媛喝不惯。秋云,
去换一盏碧螺春来。”林月儿却摆摆手:“不用麻烦了,白水就成。”她转向我,
眼神亮得惊人,“娘娘,其实人早上起来,喝点温白开对身体最好,比什么茶啊汤的都强。
”这下,连那些装鹌鹑的妃嫔们都忍不住吸气了。我端着茶盏的手指微微一顿,指尖温热,
心里却有点想笑。有趣,这位太子爷从江南带回来的“奇女子”,果然不同凡响。
太子说她“率真烂漫,与众不同”,如今看来,岂止是与众不同。“林良媛见识独到。
”我搁下茶盏,瓷器相碰,发出清脆一响,“不过宫中规矩,晨起奉茶是定例。你的心意,
本宫领了。”她似乎还想说什么,但觑了眼四周那些或鄙夷或看好戏的眼神,终究是撇撇嘴,
没再开口。请安散了,人潮退去,留下满室过于浓郁的香气和令人疲惫的安静。
秋云一边替我卸下那支沉重的凤钗,一边忍不住低声道:“娘娘,那林良媛也太没规矩了!
太子殿下竟也由着她!”我揉了揉发酸的脖颈,
看着镜中卸去钗环后显得清淡几分的面孔:“殿下喜欢,便是她的规矩。
”“可她也太张狂了!今日竟敢如此顶撞您,明日还不知要如何呢!奴婢听说,
她昨儿在花园里,竟跟太子殿下说什么……人人平等?还指责宫里的礼仪是‘封建糟粕’?
真是疯了!”人人平等?封建糟粕?我轻轻嗤笑一声。这话,倒是有几分耳熟。很多年前,
似乎也有个人,用同样亮晶晶的眼睛,说着类似惊世骇俗的话。只是那人早已成了一抔黄土,
坟头的草,怕是都有一人高了吧。“由她去。”我淡淡道,“树大招风,
她既想当这出头椽子,便要做好先烂的准备。咱们,只管‘贤良’便是。”接下来的日子,
东宫因着林月儿的到来,热闹了许多。她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,激起的何止是涟漪。
今天听说她在御花园里带着宫女太监们玩什么“丢手绢”,嘻嘻哈哈,全无体统。
明日又闻她下厨给太子做了一碗叫做“方便面”的怪东西,据说香气扑鼻,殿下竟全用了。
她还鼓捣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,比如能在夏日制出冰块的“硝石制冰”,
比如一种改良的纺车,据说效率颇高,内务府都惊动了。太子萧景宸显然对她着迷得很,
赏赐流水般送入她住的“揽月阁”,几乎夜夜留宿。东宫的风向,似乎悄悄变了。
那些原本还算安分的妃嫔们,开始坐不住了,明里暗里的酸话、绊子,层出不穷。
林月儿起初似乎吃了些亏,但她很快反击,手段直接又泼辣,几次下来,
竟也没人能真正奈何她。而我,依旧是那个最贤良的太子妃。谁受了委屈来哭诉,
我温言安抚;谁犯了错被林月儿揪住,我按宫规处置,不偏不倚。
太子来我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,偶尔来了,言谈间也总离不开“月儿如何如何新奇有趣”,
我低眉顺眼地听着,适时露出恰到好处的、略带一丝失落又强撑大度的笑容,劝他雨露均沾。
他有时会看着我,眼神复杂,似有怜惜,又似有审视,最终只化作一句:“知微,
你总是这般懂事。”我懂事。我必须懂事。从我十岁那年,被钦定为太子妃的那一天起,
“贤良淑德”就成了烙在我骨子里的印记,十年了,早已血肉相连。只是无人看见时,
我会坐在窗前,看着庭中那株母亲亲手种下的西府海棠。母亲去世得早,
我对她的印象已经模糊,只记得她有一双特别亮的眼睛,
和偶尔会冒出来的、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奇妙话语。父亲很爱她,爱到在她去后,性情大变,
从一个温文尔雅的文臣,渐渐变得沉默冷硬,手握权柄。林月儿的出现,像一道刺目的光,
照进了我早已习惯的晦暗生活。她那些离经叛道的言行,偶尔会让我想起母亲模糊的影子,
但更多的时候,是一种冰冷的审视。我看得出,她瞧不起我们,瞧不起这宫里的每一个人,
包括太子。她仰仗的,是她脑子里那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,是太子对她的新鲜和纵容。
但她不懂,这深宫里的游戏规则,从来不是比谁更“奇”。转眼到了中秋宫宴。这是大事。
帝后、宗亲、重臣、命妇齐聚,一举一动都关乎皇家颜面。我提前半月便开始操持,
事无巨细,务必妥帖。林月儿似乎也消停了几天,没闹出什么动静。
宫宴设在太液池畔的麟德殿,明月高悬,灯火如昼,丝竹悦耳,觥筹交错。
我身着太子妃冠服,坐在太子下首,保持着无可挑剔的仪态,接受着或真诚或虚伪的恭维。
目光偶尔掠过对面的席次,看见林月儿穿着一身改良过的、袖口收紧的宫装,
正兴致勃勃地跟邻座一位郡王说着什么,手舞足蹈。酒过三巡,气氛愈加热络。
皇后大约是高兴,笑着对太子道:“听闻你宫里那位林良媛,颇有些巧思,
弄出不少新鲜玩意儿?今日佳节,不如让她也出来,助助兴?”太子看向林月儿,
眼中带着鼓励和骄傲。林月儿站起身,大大方方行了个礼,声音清亮:“回皇后娘娘,
妾身近日编排了一支舞,想献给陛下、娘娘,恭贺佳节。”帝后显然颇有兴致,含笑允了。
乐声起,并非宫中常用的典雅曲调,而是带着异域风情的、节奏鲜明的鼓点。
林月儿翩然至殿中,随着鼓点扭动腰肢,挥动水袖。起初动作还算含蓄,渐渐便大胆起来,
旋转、下腰、抛袖,眼神流转,顾盼生情。那舞姿热烈奔放,
与周遭庄重华贵的氛围格格不入,却又带着一种原始的、蛊惑人心的力量。
席间已有年长的宗亲皱起眉头,命妇们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。太子却看得目不转睛,
嘴角含笑。一舞毕,林月儿气息微喘,脸颊泛红,更添艳色。她盈盈下拜,目光却扫过我,
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挑衅。殿内静了一瞬,随即响起几声零落的喝彩,多是年轻子弟。
帝后笑容淡了些,但仍是颔首表示嘉许。林月儿却没有立刻退回座位,她抬起头,
朗声道:“陛下,娘娘,此舞需双人共舞,方能尽显其妙。妾身一人独舞,终是少了些意趣。
”她顿了顿,视线精准地落在我身上,笑容甜美而无辜,“久闻太子妃娘娘德才兼备,
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想来舞艺亦是不凡。不知娘娘可否赏脸,与妾身共舞一曲,
为陛下娘娘助兴?”嗡——!我听见自己脑子里某根弦崩断的声音。殿内彻底安静下来,
落针可闻。所有人的目光,如同聚光灯一般,钉死在我身上。
惊愕、诧异、玩味、幸灾乐祸……无数情绪在那些目光中翻滚。双人舞?
还是与一个刚刚跳了如此艳舞的良媛?在这百官命妇齐聚的中秋宫宴上?
这是要将我这位太子妃的脸面,扔在地上踩,还要碾进泥里。我猛地抬眼,看向太子。
他脸上有一闪而过的错愕,随即微微蹙眉,似乎觉得不妥,但嘴唇动了动,
却没有立刻出声阻止,反而看向了林月儿,眼神里竟有一丝……无奈和纵容?心,
像被浸入了腊月的冰湖,一直沉,沉到底,冷得发疼。我站起身。华服沉重,
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我一步一步,走到殿中,向御座上的帝后深深下拜。抬起头时,
脸上已失了血色,眼眶不受控制地泛红,泪水积聚,摇摇欲坠。“父皇,母后,
”我的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,却足够清晰,传遍寂静的大殿,“林良媛之舞,新颖别致。
然……然此等舞姿,实非儿媳所能。儿媳身为太子妃,代表皇室颜面,
若于大庭广众之下……行此……此等举动,恐惹非议,有损天家威仪。此非舞艺高低,
实乃……礼法纲常所在。”我深吸一口气,泪水终于滚落,划过冰凉的脸颊,
“求父皇、母后体恤,恕儿媳……不能从命。”这是我十年太子妃生涯中,
第一次在公开场合,如此直白地拒绝,如此“失态”。
我将“屈辱”和“坚守礼法”明明白白写在脸上。殿内响起压抑的吸气声。
帝后的脸色沉了下来。皇后看向太子的眼神,已带上了严厉。太子萧景宸的脸色也变了。
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如此反应,更没想到我会当众哭诉。他猛地站起身,快步走到我身边,
伸手似乎想扶我,却又僵住。他看了眼还在殿中站着的林月儿,
又看了眼泪眼婆娑、浑身散发着“贞烈不屈”气息的我,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“知微,
”他压低声音,带着不耐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恼火,“不过是一支舞,月儿也是一片好心,
你何必如此……”“殿下!”我抬起泪眼看他,声音凄楚,“臣妾知道林良媛率真,
无有坏心。可此地是麟德殿,今日是中秋国宴!满朝文武、宗亲命妇皆在!
臣妾若今日在此……他日史笔如铁,如何书写?天下人又将如何看待东宫,看待殿下?
臣妾……臣妾宁受责罚,也绝不敢行此有辱门风、玷污殿下清誉之事啊!”说到最后,
已是哽咽难言,身形摇摇欲坠。我这番话,
扣死了“国体”、“礼法”、“太子清誉”几顶大帽子。太子再偏宠林月儿,
也不敢当众说这些不重要。果然,萧景宸语塞了,脸色阵青阵白。御座之上,皇帝终于开口,
声音威严,听不出喜怒:“太子妃所言,不无道理。林氏,你退下吧。太子,扶你妃子回座。
”一锤定音。林月儿张了张嘴,似乎还想辩解,被太子一个眼神制止,只得悻悻退下,
脸上满是不服和委屈。太子伸手扶住我的胳膊,力道有些重。我借着起身的力道,微微侧头,
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耳语,颤声补了一句:“殿下若觉得臣妾迂腐,
扫了您的兴致……臣妾,任凭处置。” 眼泪适时地,又滚落一串。
萧景宸扶着我的手僵了一下。他没再说话,只是扶着我,一步一步走回座位。他的掌心很烫,
可我却只觉得那股凉意,从心里蔓延到了四肢百骸。坐回位置,我低垂着头,
用袖子轻轻拭泪,肩膀微颤,一副受尽委屈却强自忍耐的模样。眼角的余光,
瞥见林月儿坐回原位后,狠狠剜了我一眼,嘴唇抿得死紧。而太子,沉默地喝着酒,
再没往她那边看一眼。宫宴的后半程,气氛有些微妙。帝后早早起驾回宫,
众人也识趣地陆续散去。回到东宫,太子径直去了书房,没来我的寝殿,也没去揽月阁。
秋云替我卸妆时,手都在抖,又是后怕又是气愤:“娘娘,您今日真是……太险了!
那林良媛分明是故意的!她想让您当众出丑!”我看着镜中卸去脂粉后苍白却平静的脸,
拿起梳子,慢慢梳理着长发。“是啊,她是故意的。”我轻声道。
“那您还……”“我不当众‘受辱’,如何显得她‘不知轻重’?我不哭不诉,
如何让父皇母后、让满朝文武看清,是谁在不顾体统,是谁在搅乱纲常?
”铜镜映出我的眼睛,里面没有泪光,只有一片冰冷的清醒,“太子可以宠她,可以纵她,
甚至可以为她破例。但在皇家脸面和礼法大防面前,她那点‘新奇’和‘率真’,不值一提。
”秋云似懂非懂,但看我神色平静,也渐渐安下心来。那一夜后,东宫表面恢复了平静,
但暗流愈发汹涌。太子来我这里的次数多了些,虽不说话,有时只是坐坐,但态度明显缓和。
赏赐也多了,大约是补偿。而对林月儿,虽未明着冷落,
却也未再如之前那般毫无原则地纵容。林月儿似乎安分了一段时间。但她那样的人,
怎么可能真正安分?深秋某日,她突然病了,病势来得凶猛,上吐下泻,
太医看了说是吃了不洁之物。揽月阁的宫人被拷问,
最后竟查到我小厨房一个负责采买的老太监身上,说是收了宫外的钱,
在林良媛的饮食里动了手脚。人证物证“确凿”。太子震怒,下令彻查。那老太监熬不住刑,
竟“招认”是受了我宫中一个二等丫鬟的指使,而那丫鬟,又“供出”是得了我的默许。
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我被“请”到太子书房时,萧景宸脸色铁青,将供词摔在我面前。
“沈知微!你还有什么话说?月儿究竟哪里得罪了你,你要用如此下作手段害她性命?!
”我看着地上散落的纸张,又抬头看他。他的眼中,有愤怒,有失望,
还有一种被背叛的痛心——为了那个林月儿。心底那最后一丝微末的、属于十年夫妻的情分,
在这一刻,彻底凉透了,碎成了齑粉。我没有辩解,没有哭诉,只是缓缓跪下,
背脊挺得笔直。“殿下既已认定是臣妾所为,臣妾无话可说。”我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,
“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殿下要如何处置,臣妾领受便是。”我的平静似乎激怒了他。
他猛地一拍桌子:“领受?你以为我不敢罚你?!传令,太子妃沈氏,善妒失德,言行有亏,
即日起禁足昭阳殿,无令不得出!宫中事务,暂交……林良媛协理!”林良媛协理东宫?
一个入宫不到半年的良媛?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,也是对我这个太子妃最彻底的羞辱。
消息传开,阖宫哗然。但太子正在气头上,无人敢劝。我被“送”回昭阳殿,宫门落锁。
秋云气得直哭,我却只觉得轻松。终于,不用再戴着那副贤良面具,对着一群心思各异的人,
扮演那令人作呕的“和睦”了。禁足的日子清静得很。除了送饭的粗使太监,再无人打扰。
我有时看书,有时抄经,更多的时候,只是看着庭中那株海棠树,叶子已经落尽,
枝干嶙峋地刺向灰白的天空。父亲那里,该得到消息了吧。深冬的第一场雪落下时,
禁足尚未解除。但宫外的消息,却像长了翅膀一样,悄悄飞了进来。北方匈奴异动,
边关告急。朝堂上主战主和吵成一团。陛下有意派兵增援,点将之时,
我那已多年不掌兵权、挂着太傅虚衔的父亲,沈稷,竟主动请缨。举朝皆惊。
谁不知道沈太傅是文臣出身,虽早年随军有些阅历,但毕竟多年未涉军旅。
太子一党极力反对,认为此举儿戏。但皇帝在沉吟数日后,竟准了。任命沈稷为北征大元帅,
即日点兵出征。消息传到东宫时,我正在窗边看雪。秋云凑在我耳边,低声说着听来的细节,
眼睛亮晶晶的:“娘娘,老爷他……真的能行吗?听说朝上好多人等着看笑话呢。
”我没说话,只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雪花,看着它在掌心迅速消融,变成一滴冰冷的水。
看笑话?或许吧。但你们很快,就笑不出来了。父亲离京那日,我没有去送,也不能去送。
只是听说,场面很是冷清,太子称病未至,百官也只寥寥。父亲骑着马,穿着锃亮的铠甲,
在漫天风雪里,回头望了一眼皇城的方向,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一刻,
我仿佛能看见他花白的胡须上凝结的冰霜,和那双沉静眼眸深处,酝酿了十余年的风暴。
父亲出征后,东宫的气氛变得有些怪异。太子对我的禁足令并未撤销,
但看守明显松懈了许多。林月儿“协理”宫务,起初兴致勃勃,搞了许多“革新”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