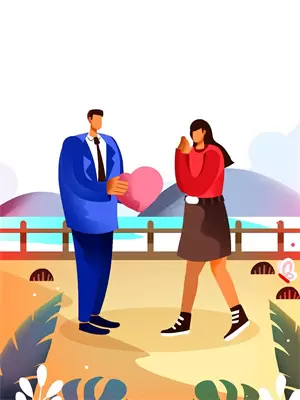他说想要成婚对食,和心爱之人相守一生。
我便自备嫁妆,等着做他的妻。
梁君沉却拧眉接过我熬坏眼睛绣好的喜服:“阿瑾是尚宫局主事,见过无数至宝华服。
这手艺太过低劣,她瞧不上眼的。”
“我苦练男女之事便是要向阿瑾证明,就算我是天阉之人也能让她享受极乐。”
原来梁君沉床笫之间对我的极尽讨好温柔,都是为了更熟练地去伺候另一个人。
而在他唇舌指尖下沉沦的我,早已忘了自己是金枝玉叶的公主。
我主动和亲嫁去云藏,他竟也在和亲使团。
洞房花烛夜,夫君剥下我的外衫吻过来,梁君沉洒下喜果:“早生贵子,恩爱白头。”
一抬眸我们四目相对,他惊愕的眸光刹那间支离破碎。
——冰凉的酒水倒在身上,很快又被梁君沉温热的唇舌清理干净。
经过这一年的恩爱缠绵,他早已对我了如指掌,知道怎样最能让我沉沦。
梁君沉将酒壶高高举起,酒水洋洋洒洒流入口中。
分明是粗鲁的动作,由他做起来却有种风华绝代的韵味。
他喑哑低沉的嗓音更是令我入迷:“这九酝春酒,不及你身上自带的琼浆玉露醉人。”
我在梁君沉唇舌的轻描淡写中几近昏厥。
而意乱情迷过后的他眉眼平淡,连繁复的飞鱼服都不曾有半丝褶皱。
“令昭,我也想像寻常男子一般成婚,与心爱之人白头到老。”
梁君沉语气是惯常的平淡,但我却从中听出了期盼与渴望,一瞬间脸又红又烫。
“好,那成婚事宜就由我来操办。”
我答应得痛快,梁君沉却迟疑了:“令昭,我是天阉之人。
你真的觉得,与我共度一生不是煎熬吗?”梁君沉是东厂都督,但与其他净过身的太监不同。
他是天阉之人,身体并未残缺。
在他绯红勾人的目光下,我颤着手拢起衣裳:“你并不比寻常男子差,能和你共度余生我求之不得。”
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,蜻蜓点水般在我嘴角印下一吻:“那大婚就辛苦你来操办了。”
为了与梁君沉的大婚,我白天忙得脚不沾地,晚上还要挑灯绣喜被、喜服和喜帕。
熬得两眼发黑,终于赶在半个月内给自己准备好了嫁妆。
这夜与梁君沉温存过后,我忍不住将喜服展开在身前比较:“这套喜服很衬人,穿上以后一定很好看。”
他意味不明地‘啧’了声,随即拧眉接过我手中的喜服。
只是扫了一眼,就嫌弃地将喜服扔在地上:“阿瑾是尚宫局主事,见过无数至宝华服。
这手艺太过低劣,她瞧不上眼的。”
我脑袋轰得一声炸开,怔怔重复一遍他口中那个名字:“阿瑾?”“是,我即将求娶尚宫局主事柳瑾。”
说罢梁君沉自嘲地按了按眉心,“事情没办好也怪不得你,是我忘了你在进宫前只是个小乞丐。”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更不敢相信日日与我翻云覆雨的梁君沉想娶的一直另有其人。
梁君沉宠溺的揉了揉我的腰窝:“不用自责,我不该将阿瑾的嫁妆交给你来操办。
毕竟你只是草间萤火,怎能窥探她明珠的光亮。”
在他温柔的安抚下,我反而浑身温度尽失,心脏痛得骤缩几下。
我浑浑噩噩拿起喜服往外走,却被梁君沉从背后拦腰搂住:“外面天凉,你要去哪?”而我嗓音轻得语不成句:“这件喜服配不上柳主事,我拿到外面去处理掉。”
梁君沉含着我的耳垂轻咬几下:“处理完早些回东厂来,皇宫不是你能乱跑的地方。”
灼热的炉子前,我将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喜服扔进火里。
看着被火舌吞噬的喜服,我想起自己因为逃婚流落街头,被一身大红飞鱼服的梁君沉当作小乞丐捡回东厂那一日。
他妖冶绝美,剑眉横直入鬓平添睥睨天下的霸气。
穿上飞鱼服后更是桀骜恣意,我第一眼便就此沦陷。
于是我隐瞒身份,义无反顾跟着梁君沉回到这座自己拼死逃离的黄金囚笼。
他与我做最亲密的夫妻之事,在床笫之间对我百般温柔用心。
可原来,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他爱我。
我没有听梁君沉的话烧完喜服就回东厂,而是径直去了养心殿,皇帝的寝宫。
“父皇,女儿愿意去云藏和亲。
只要女儿在世一日,便会尽到一国公主的职责,保边疆一日太平。”
父皇轻轻扶起我,叹息一声:“若非朕授意,你以为自己真能长出翅膀隐匿行踪?”“边疆重要,但朕的女儿更重要。
和亲使者还有七日抵达京城,你若反悔不出现,父皇会另外安排人替你上轿。”
我心事重重地回到东厂,就见昔日阴气沉沉的地方张灯结彩一片喜气。
一众锦衣卫众星捧月般围着正在亲自清点聘礼的梁君沉:“厂督,您与令昭姑娘不是对食吗?怎么现在求娶的却是柳主事?”闻言我心头一颤,下意识攥紧五指紧盯着梁君沉。
因为我也很想知道,这一年与我纵情欢爱对他来说算什么。